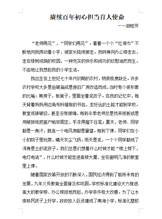原则理论的宪法适用研究(2)
若水分享
1147
四、宪法原则解释法中冲突的解决
依循前述原则理论的有关知识,本文认为,宪法解释的原则解释法的中心问题在于:一是如何处理个案中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个案中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之间的关系?
(一)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的冲突
这个问题主要是指当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不一致时,该优先适用宪法原则还是优先适用宪法规则?在什么情况下优先适用宪法原则?在什么情况下优先适用宪法规则?
葛洪义教授认为,“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在有法律规则的情况下,必须适用法律规则,一般不能适用法律原则,除非能够证明规则的适用其结果是明显荒谬的,违反了法治基本精神。”[27]相对于原则而言,规则具体明确,而原则抽象模糊,在既有原则又有规则且规则不抵触原则时,应当优先适用规则。在出现无规则可适用的情况下,原则才可以作为弥补“法律漏洞”的手段起作用。因此,在穷尽规则之前不能适用原则。这种要求在宪法解释中也是适用的,即一般而言应当在穷尽宪法规则之后,方能适用宪法原则。但宪法解释中的原则解释方法主要涉及的是在无宪法规则时、或宪法规则的内容与宪法原则相冲突或矛盾时的情况。虽然宪法规范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特征,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及其发展变迁的快速性使得宪法规范也不可能将一切事件囊括于宪法规则之中,宪法的开放性特征是通过宪法的原则性规范来体现的。因此,当出现尚无宪法规则的时候,应以宪法原则作为宪法解释的标准。宪法规则是在宪法原则指导下制定的,宪法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宪法原则,宪法规则一般来说与宪法原则是一致的。但宪法规则的适用有可能因应时代环境的变迁或特定事件的需要而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或者是通过修宪法来完成,或者是宪法规则在适用时被人们赋予了新的含义来完成,这都有可能导致宪法规则背离宪法原则的情况出现。当宪法规则与宪法原则的含义不一致时,根据宪法原则的指导和评价功能的要求,应以宪法原则作为宪法解释的参照。
但宪法原则与宪法规则冲突的解决还不止于这么简单,因为宪法原则的多样性使问题变得复杂化了。阿列克西认为,在具体案件中若涉及规范冲突时,原则P1虽然可被强度较高的原则P2所超越,然而如果相冲突的是原则P1与支持该规则的原则P2,即使原则P1比原则P2强度高,也不能无条件地推论出原则P1应优先适用的结论,因为原则P1除了必须与支持该规则的原则P2相衡量外,还须与一些“形式原则”相衡量,如“通过正当权威所制定的规则必须遵守”、“不得无理由地偏离素来就有的法律实务”等形式原则。[28]也就是说,原则P1要优先于原则P2,它不仅在内容上要强过原则P2,而且其强到必须强到足以排除支持原则P2的形式原则。
试举一例以说明之,根据我国有关宪法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权变通执行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宪法》第115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与这一宪法规则有关的宪法原则是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宪法》第5条)和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宪法》第4条),从这两个宪法原则的重要性即强度上看,国家法制统一原则高于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因为变通规定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该变通执行的宪法规则虽与法制统一的宪法原则相冲突,但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宪法原则又支持该宪法规则,所以即使法制统一原则高于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也不能得出无条件地推论出法制统一原则优先于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因为法制统一原则除了与民族区域自治原则相衡量外,还须与一些形式原则——如“通过正当权威(全国人大)制定的规则必须遵守”、“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相衡量。这样,假使法制统一原则要在个案中优先于民族区域自治原则,除了在内容上要强过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其强度还必须足以排除支持民族区域自治原则的形式原则,否则,即使法制统一原则在内容上强过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也不能无条件地优先于后一原则。
(二)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的冲突
这个问题就是指在原则解释法中,当出现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相冲突时应该优先适用哪一原则?有人试图通过对原则排序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正如舒国滢教授所说的那样,无论是通过事实维度还是通过规范维度来为原则排序,都难以真正解决问题,且人为地为原则确定自始先后高低的位序,还可能导致“价值专制”。 [29]
根据前述德沃金原则理论的相关知识,原则冲突不会像规则冲突那样导致其中之一无效,而是在个案中通过对它们的份量和重要性的强弱进行衡量后使其中一个原则具有优先性,且这种优先性只是相对于该案而言,在另一案件中,这两个原则之间的优先关系有可能反过来。但德沃金没有指出如何衡量相互冲突的原则的份量这一核心问题。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教授所说,“衡量”也好,“称重”也罢,这些都是形象化后的说法,于此涉及的并非数学上可得测量的大小,毋宁是评价行为的结果,此等评价最困难之点在于:其并非取向于某一般性的标准,毋宁须同时考量当下具体情况。[30]
由于原则与规则都有缺陷,即规则虽然具有严格拘束性,但在不存在相关规则的情况下就会出现法律漏洞,而原则虽然具有开放性,但欠缺安定性。为弥补二者的缺陷,价值的引入就成为及时且必要的了。[31]因此,无论是规则冲突还是原则冲突说到底都是价值的冲突。许多学者都强调运用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来解决原则冲突,这种“法益衡量”根本上说是一种价值衡量,是在具体情况下基于某种考虑而对涉案问题作价值上的权衡和取舍,“就是说,互相冲突的原则必须互相衡量或平衡,有些原则比另一些原则有较大的分量。”[32]既然价值衡量是解决原则冲突所不可避免的选择,那么,保证衡量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就成为引人注目的关键了。
阿列克西认为,要解决两个原则在同一个案中相冲突时的“紧张关系”,必须根据“冲突法则”来判断哪个原则优先、哪个原则必须退让。他认为,解决原则冲突须运用“衡量决断模式”,要使这种衡量决断模式避免恣意和主观臆断的危险,就须运用“衡量证成模式”,以使法益衡量具有合理性。“衡量证成模式”的合理性奠基于其说理证成之上,除了一般论证形式,如解释的标准、释义学的论证形式、判例论证、一般实践论证、经验论证之外,还会运用专门针对衡量的独特论证形式,即原则P1不实现或受阻碍的程度越高,实现原则P2的重要性就必须越大。阿列克西称此为“衡量法则”。根据该“衡量法则”,衡量不是为追求此价值而轻率地牺牲彼价值的程序,也不是抽象的不加区分的决定程序,衡量的结果是运用“冲突法则”产生的,所获得的是针对具体个案的规则。衡量的任务在于“极佳化”原则的使用,即根据法律和事实可能性尽可能地实现原则的内容,因此衡量也符合常被强调的宪法解释的“实践的和谐”原则。[33]
值得注意的是,阿列克西的“衡量法则”的最终目的在于使对相互冲突的原则的衡量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来源于对原则的优先关系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而这又有赖于“极佳化”原则这一任务的实现。这里的“极佳化”不是指使原则的内容在社会现实中得到最大化的实现,因此必须首先准确理解他所谓的“极佳化诫命”这一概念,才能真正作到原则衡量的合理性。这一概念中的“极佳化”不是“最大化”,而是“尽可能”的意思。也就是说,原则内容只能以或多或少的方式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而其实现程度的大小取决于法律和事实要件。所以,一个原则在具体案件中取得优势,并非由其自身决定的,并非绝对的优势,而是在个案中的相对优势,其内容实现的程度不会因一个案件而固定下来,它会随法律和事实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这里仍以前述“西难重组”案为例加以说明。联邦宪法法院在审理第二重组法案时,涉及处理联邦主义原则与民主原则的冲突。在解决这两个宪法原则的冲突时,宪法法院确定了“更广泛的整体利益”作为法益衡量的“优先条件”。由此根据“冲突法则”,联邦主义原则在“更广泛的整体利益”这个条件下优先于民主原则,所以民主原则必须退让,其法效果就是第二重组法案合宪,驳回巴登州政府的违宪主张。在这个过程中,宪法法院运用了“衡量证成模式”,不仅运用了一般论证形式,还运用了专门针对衡量的独特论证形式,即“衡量法则”。其一般论证是:作为不可侵犯的原则,《基本法》第79条仅保障联邦必须“分解为州”,对现存各州及其州界,《基本法》并未包含任何保障,相反,《基本法》采纳了“可变的联邦国体”,从第29条和第118条,它允许州的边界改变及联邦领土之重组,即使违反该州人民的意愿,这种重组仍可以实现;从议会理事会在制定《基本法》时的讨论、以往的公共讨论,以及现在三州政府之间的协商中,我们得知人民对西南地区的公法现状表示普遍不满,因而立即重组的时机业已成熟,迅速与简便的重组是众望所归,它不能被一州人口的反对所挫败;作为联邦的州成员,巴登州并不自主或独立,而是联邦的一部分,其主权在各个不同方面受到联邦秩序的限制。
其专门针对衡量的独特论证是:对于联邦领土的重组案件,问题的形式决定:为了一项更为广泛的整体利益,一州人民的自决权应受到限制,这就是说,联邦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大于巴登州一州人民的自决权利益,因此巴登州一州的民主权利须让位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联邦的利益。于是,联邦宪法法院在通过“冲突法则”建立了一个可资涵摄的规则后,再通过全面而充分的论证,得出联邦主义原则优先于民主原则的结论,从而驳回了巴登州政府的请求。[34]
总之,在宪法解释中,当出现两个宪法原则相冲突时,必须通过“冲突法则”来决定这两个原则衡量的结果,必须运用“衡量证成模式”来排除衡量结果的恣意以使其具有合理性,使这种衡量符合“衡量法则”的要求。
【注释】
[1]参见刘国:《宪法解释的特质》,《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该部分材料主要引自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以下。
[3]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704页。
[4]参见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页。
[5]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创造性地建立了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制度。但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案时所处地位不同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西南重组”案中无须对《基本法》作出创造性解释。因为在《基本法》产生之时,司法审查制度早已在大洋彼岸确立,且联邦《基本法》第93条明确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6]比如相对于“权力分立原则”,就有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与制衡形态,这些形态皆由更具体的宪法条文来做进一步的规定。
[7]比如“诚实信用原则”,相对于其他的民法规定,该原则的内容比较抽象,也可说比较空泛,单从该原则很难得出具体案例的判断标准。
[8]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9]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100页。
[10]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8页。
[11]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12]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13]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10-11页。
[14]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12页。
[15]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18-20页。
[16]实际上可以说,宪法原则解释法的采用可以追溯到1803年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在该案中,马歇尔法官在美国宪法并未明文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有司法审查权的情况之下,推导出联邦最高法院有解释宪法和审查国会立法是否违宪的权力,就是通过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解释宪法而得出的最终结论。
[17]参见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26-227页。
[18]另一类是类推解释法,即对需要进行释义的条文比照最相类似的宪法条文的规定进行释义。参见莫纪宏:《宪政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19]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20]参见[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21]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3页。“作为整体的法律要求法官尽可能假设法律是由一整套前后一致的、与正义和公平有关的原则和诉讼的正当程序所构成。它要求法官在面临新的案件时实施这些原则以便根据同样的标准使人人处于公平和正义的地位。这种审判方式尊重整体性所假定的愿望,即成为一个原则社会的愿望。” [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22]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权利法案由宽泛而抽象的关于政治道德的一些原则组成,这些原则以一种极其抽象的形式囊括了政治道德的所有层面,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这些政治道德能够给个人的宪法权利提供牢固的基础。” [美]罗纳德?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23]参见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2页。
[24]李龙:《宪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25]参见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26][英]尼尔·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27]葛洪义:《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比较的研究》,《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10页。
[28]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13页。
[29]参见戚渊、郑永流、舒国滢、朱庆育:《法律论证与法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6页。舒国滢教授写道,“假如我们仅在事实维度来思考原则的位序,那么有待通过规范裁剪的事实本身不能作为判断法律原则先后高低的基准,毋宁说事实反过来求助于法律原则作为评价的标准。如果我们仅在规范维度来为法律原则排序,那么无论我们怎样精确地确定原则计算的数值,都会成为一种“不及物”的空洞的运算,难以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原则之冲突解决方案。” 见戚渊、郑永流、舒国滢、朱庆育:《法律论证与法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3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9页。
[31]在原则和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阿列克西与哈贝马斯持不同的立场。阿列克西认为,原则与价值二者有所区别,但两者也具有相似性,表现在语言使用上和冲突结构上。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29-30页。然而,哈贝马斯严格区分原则和价值,认为前者具有义务论的意义,后者具有价值论的意义,二者的区别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于它们所指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童世骏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15-316页。
[32][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宋金娜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33]参见张嘉尹:《法律原则、法律体系与法律概念》,《辅仁法学》第24期,第21-22页。
[34]参见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册·欧洲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