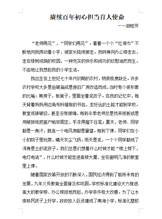讲一口中式英语没啥大不了的
若水分享
1147
英语在全世界的扩展,固然有英美前后执掌世界霸权的政治推动,英语本身的易学易用,也是一大原因。
咱就喜欢讲带有“呛你死”特色的洋泾浜英语,I speak Chinglish。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So what?
某些对学习英语愤愤不平的同志,喜欢说学了没用,学了多年,见到洋人,还是彼此听不懂。不过,学英语之前,我们就开始学普通话,而普通话按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那么,一个南方学生初到北方,别人就能听懂他的“普通话”了?你去北京郊区找个农村老头试试。这位学生需要一段时间让别人习惯他的口音,同时他也开始熟悉当地的口音。既然中国人讲普通话都有一时听不懂的问题,一时听不懂洋人或洋人一时听不懂,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曾有一位在澳洲留学的女生写信问我,为什么她听不懂教授的讲课?我说,以你雅思听力的考分,听不懂肯定不是英语水平问题,只是一时不熟悉澳洲口音罢了,过一阵子就会好的。她说,果然连美国学生也有抱怨听不懂的。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南非英语,等等,各有各的口音;一国之内,美国的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口音也不同,小布什就喜欢讲一口德克萨斯牛仔英语。哪怕跟着唱片学了流利伦敦音,初到美国,照样可能一时听不懂。
像纽约这种各国移民的大熔炉,英语口音更是五花八门。大公司主管雇着只讲伦敦音的英国女秘书,独立两百年后,以母国标准音接电话,仍然是 prestige 的标志。但街上的人们,却模仿黑人口音,以双重否定作否定,以“不合逻辑”(按逻辑,负负得正,双重否定相当于肯定)为 fun。任何一家市场里,你都可以听到德国人和俄国人讲大舌头卷卷的英语,韩国人和日本人讲长元音特别多的英语,伊朗人和阿拉伯人讲鼻音很重的英语,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讲调门怪怪的英语。
口音如此“乱七八糟”,美国人和英国人居然不在乎?Well,英语本来就是大杂烩。历史上,英格兰受过罗马人、北欧海盗和法国人三次入侵,英语也和入侵者的语言有过三次大混血。混血的结果是语音和语法变得简单而词汇却异常丰富。按语言学分类,英语和德语是近亲。德语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性指名词分阳性、阴性和中性;数指单数和复数;格指作主语或作宾语等不同语法成分时词尾有不同,德语有四种格),动词与形容词的词尾变化必须与名词的性数格匹配。但这些复杂的德语语法规则,除了变得远为简单的数的变化,在英语里几乎全部消失了。
混血使语言变得简单,混血的语言——就像生物学有“杂种优势”一说——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英语在全世界的扩展,固然有英美前后执掌世界霸权的政治推动,英语本身的易学易用,也是一大原因。正如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官话”(普通话),本是古汉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大混血之后的产物。混血的结果是元音少了,辅音少了,声调也少了,短促的入声干脆消失,所以流行起来也方便,成了中国第一方言,虽然这流行也有历朝定都北京的政治推动。
当今全球化时代,英语大概面临着新的混血。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是公认的英文大家,却在他的小说里大量运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分别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主要语言)词汇。在美国,曾受布什夫人推荐的南方著名作家科马克·麦卡锡,在他的“边界”三部曲里频频搬用西班牙语。两国读者无所谓。就像我们读湖南作家的作品,“堂客”来“堂客”去的,翻了几页,自然知道堂客就是老婆。
所以,讲讲青格利希没什么了不起,从英语历史看,说不定还会丰富英语的表达。说不定有一天,纽约某位白大哥去抢《星球大战》第100集首映票,到电影院门口一看,他耸耸肩摊开双手:Man mountain man sea,today no see,tomorrow same see。喔,这是中国式的洋泾浜英语嘛:人山人海,今天不看,明天同样看。混血语言,简单新鲜。
咱就喜欢讲带有“呛你死”特色的洋泾浜英语,I speak Chinglish。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So what?
某些对学习英语愤愤不平的同志,喜欢说学了没用,学了多年,见到洋人,还是彼此听不懂。不过,学英语之前,我们就开始学普通话,而普通话按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那么,一个南方学生初到北方,别人就能听懂他的“普通话”了?你去北京郊区找个农村老头试试。这位学生需要一段时间让别人习惯他的口音,同时他也开始熟悉当地的口音。既然中国人讲普通话都有一时听不懂的问题,一时听不懂洋人或洋人一时听不懂,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曾有一位在澳洲留学的女生写信问我,为什么她听不懂教授的讲课?我说,以你雅思听力的考分,听不懂肯定不是英语水平问题,只是一时不熟悉澳洲口音罢了,过一阵子就会好的。她说,果然连美国学生也有抱怨听不懂的。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南非英语,等等,各有各的口音;一国之内,美国的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口音也不同,小布什就喜欢讲一口德克萨斯牛仔英语。哪怕跟着唱片学了流利伦敦音,初到美国,照样可能一时听不懂。
像纽约这种各国移民的大熔炉,英语口音更是五花八门。大公司主管雇着只讲伦敦音的英国女秘书,独立两百年后,以母国标准音接电话,仍然是 prestige 的标志。但街上的人们,却模仿黑人口音,以双重否定作否定,以“不合逻辑”(按逻辑,负负得正,双重否定相当于肯定)为 fun。任何一家市场里,你都可以听到德国人和俄国人讲大舌头卷卷的英语,韩国人和日本人讲长元音特别多的英语,伊朗人和阿拉伯人讲鼻音很重的英语,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讲调门怪怪的英语。
口音如此“乱七八糟”,美国人和英国人居然不在乎?Well,英语本来就是大杂烩。历史上,英格兰受过罗马人、北欧海盗和法国人三次入侵,英语也和入侵者的语言有过三次大混血。混血的结果是语音和语法变得简单而词汇却异常丰富。按语言学分类,英语和德语是近亲。德语名词有性数格的变化(性指名词分阳性、阴性和中性;数指单数和复数;格指作主语或作宾语等不同语法成分时词尾有不同,德语有四种格),动词与形容词的词尾变化必须与名词的性数格匹配。但这些复杂的德语语法规则,除了变得远为简单的数的变化,在英语里几乎全部消失了。
混血使语言变得简单,混血的语言——就像生物学有“杂种优势”一说——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英语在全世界的扩展,固然有英美前后执掌世界霸权的政治推动,英语本身的易学易用,也是一大原因。正如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官话”(普通话),本是古汉语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语言大混血之后的产物。混血的结果是元音少了,辅音少了,声调也少了,短促的入声干脆消失,所以流行起来也方便,成了中国第一方言,虽然这流行也有历朝定都北京的政治推动。
当今全球化时代,英语大概面临着新的混血。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是公认的英文大家,却在他的小说里大量运用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分别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主要语言)词汇。在美国,曾受布什夫人推荐的南方著名作家科马克·麦卡锡,在他的“边界”三部曲里频频搬用西班牙语。两国读者无所谓。就像我们读湖南作家的作品,“堂客”来“堂客”去的,翻了几页,自然知道堂客就是老婆。
所以,讲讲青格利希没什么了不起,从英语历史看,说不定还会丰富英语的表达。说不定有一天,纽约某位白大哥去抢《星球大战》第100集首映票,到电影院门口一看,他耸耸肩摊开双手:Man mountain man sea,today no see,tomorrow same see。喔,这是中国式的洋泾浜英语嘛:人山人海,今天不看,明天同样看。混血语言,简单新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