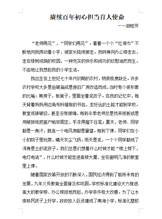翻译漫谈(一)翻译的乐趣
若水分享
1147
我从小就喜欢翻译。记得在青岛上中学的时候,曾把英语课本里的故事译成中文,不是为了发表,纯粹是觉得好玩儿,而且有一种成就感。
大学毕业后,留在北外当老师,后来有幸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著作的翻译和修订工作,参加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当时我觉得学习外语,能做这样的工作,是无上的光荣,这种感受也鞭策我努力钻研。
有一天,我看到这样一句话:
“吃一堑,长一智。”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没想到天下竟有这样好的译文,它本身就像一句谚语,然而它又与原文如此接近,如此吻合,使我惊讶不已。
后来我又看到这样一句话:
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To win this victory will not require much more time and effort, but to consolidate it will.
原文里重复出现的词语,译文没有重复,一个小小的will竟然替代了原文用二十多个字表达的意思。我在这里看到了道地的英语。每当我看到这样好的译例,就回想起小时候在海边玩耍,捡拾贝壳。阳光下,那贝壳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拿在手里,别提多么高兴了。近年来,参加了几本词典的审定工作。原书都是英英词典,加上汉语译文后,变成英汉双解词典。译文对不对,顺不顺,这就是审定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
原文:The cold weather frosted up the track last night.
译文:昨晚寒冷的天气使跑道上结了霜。
改为:昨晚天气寒冷,跑道上结了霜。
原文:My toes were frostbitten from skating too long.
译文:滑冰的时间太长使我的脚趾冻伤了。
改为:滑冰的时间太长,我的脚趾冻伤了。
改动虽然不大,译文弄得比较通顺了,这也是对词典的贡献。
翻译有没有苦恼,有的。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过:“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译者这时的确感到心急如焚,焦头烂额,可是一旦找到合适的译文,就会感到格外痛快。
译者还有一种苦恼,那就是一个长篇在手久久不能完成。我译《大卫·科波菲尔》时,就有这种体会。前后三年时间,一天都不敢歇息,更谈不上娱乐。家里人抱怨,“连跟你说话的工夫都没有。”三年里,我天天跟书中的角色打交道,把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感情用汉语表现出来,他们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在快译完全书的时候,怀着沉重的心情仿佛向他们一一告别,痛苦得很呀。
几年以后,忽然有一天出版社的责编打来电话,说我的书快要出版了。我兴奋极了。取回样书的那一天,我对老伴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我已经把他接回来了,他的名字就叫“大卫”。
总之,翻译蕴藏着无穷的乐趣,等待喜欢他的人去发掘。干这一行,就要爱这一行,否则怎么能做得好呢?
大学毕业后,留在北外当老师,后来有幸参加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著作的翻译和修订工作,参加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当时我觉得学习外语,能做这样的工作,是无上的光荣,这种感受也鞭策我努力钻研。
有一天,我看到这样一句话:
“吃一堑,长一智。”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没想到天下竟有这样好的译文,它本身就像一句谚语,然而它又与原文如此接近,如此吻合,使我惊讶不已。
后来我又看到这样一句话:
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To win this victory will not require much more time and effort, but to consolidate it will.
原文里重复出现的词语,译文没有重复,一个小小的will竟然替代了原文用二十多个字表达的意思。我在这里看到了道地的英语。每当我看到这样好的译例,就回想起小时候在海边玩耍,捡拾贝壳。阳光下,那贝壳五光十色,绚丽多彩,拿在手里,别提多么高兴了。近年来,参加了几本词典的审定工作。原书都是英英词典,加上汉语译文后,变成英汉双解词典。译文对不对,顺不顺,这就是审定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
原文:The cold weather frosted up the track last night.
译文:昨晚寒冷的天气使跑道上结了霜。
改为:昨晚天气寒冷,跑道上结了霜。
原文:My toes were frostbitten from skating too long.
译文:滑冰的时间太长使我的脚趾冻伤了。
改为:滑冰的时间太长,我的脚趾冻伤了。
改动虽然不大,译文弄得比较通顺了,这也是对词典的贡献。
翻译有没有苦恼,有的。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说过:“譬如一个名词或动词,写不出,创作时候可以回避,翻译上却不成,也还得想,一直弄到头昏眼花,好象在脑子里面摸一个急于要开箱子的钥匙,却没有。”译者这时的确感到心急如焚,焦头烂额,可是一旦找到合适的译文,就会感到格外痛快。
译者还有一种苦恼,那就是一个长篇在手久久不能完成。我译《大卫·科波菲尔》时,就有这种体会。前后三年时间,一天都不敢歇息,更谈不上娱乐。家里人抱怨,“连跟你说话的工夫都没有。”三年里,我天天跟书中的角色打交道,把他们的言行和思想感情用汉语表现出来,他们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在快译完全书的时候,怀着沉重的心情仿佛向他们一一告别,痛苦得很呀。
几年以后,忽然有一天出版社的责编打来电话,说我的书快要出版了。我兴奋极了。取回样书的那一天,我对老伴说,我又有了一个儿子,我已经把他接回来了,他的名字就叫“大卫”。
总之,翻译蕴藏着无穷的乐趣,等待喜欢他的人去发掘。干这一行,就要爱这一行,否则怎么能做得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