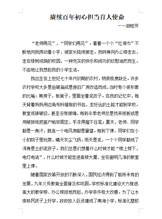旧时光里的栀子花
若水分享
1147
穿过五月的季节,走在城市的公园或花坛,细碎碎的栀子花就会在绿叶里飞舞,她们密匝匝的簇拥枝丫,热热闹闹地望着你。清香在夏季阵阵弥漫,此时的我,会一点点的晕眩,思绪慢慢缥缈,旧时光里的那些栀子花就会摇曳起来,在我的心田,在我的记忆里。
一
其实,在南方湖州长大的孩子,打小很少看见栀子花树,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儿时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去舅爷家走亲戚,舅爷离我们家几十公里,走了近乎一整天泥路的小女孩,劳顿把一份新奇和欣喜折腾得只想哭涕,我牵着妈妈的手,深一脚低一脚地走着,终于在向晚时分到达村庄。
记忆中,夕阳下的村庄很美。夏日的微风拂着田畴,禾苗轻轻荡着波浪,青山绿水里,袅袅炊烟从暮霭中升起,一份宁静和温暖让远涉的我有了归依,终于又孩子脸的笑了。
绕过长长的竹篱,我们跨进了舅爷的小院,我被一种从没看过的景致吸引,整整洁洁的庭院里,一栋四间的茅草平房,西边一座低矮的墙上爬满一架嫣红红的蔷薇花。庭院的东边,有一棵开满白色花朵的参天大树,这棵华冠丰荗的大树就是栀子花树。夕阳的金辉照在这个开满鲜花的庭院,花儿的清香幽幽飘来,我仿佛不是走入一个乡野之气的农舍,而是来到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被一种清雅、脱俗的气息围绕。
妈妈曾告诉我,外婆、舅爷的父亲曾是清朝的秀才,那份雅致遗落下来,我想是很自然的。
我很喜欢那个庭院,那棵开满栀子花的大树,很多年后,我记不清在那个庭院里很多的碎事,但清楚的记得,每天清晨我会早早的起床,站在这颗大树下仰着头,看栀子花在夏日的晨露里低眉浅笑,看她们捂着蕾儿白洁洁的开,开出芳香的味道。
二
江水、小镇。白墙黑瓦、青石板路……
这是我的故乡。在青葱的岁月我再次邂遇栀子花。
也许是女孩子爱花做梦的时季,姐妹们总爱在自家的菜园里栽种很多的花草。当缤纷的花们次第开放,兴奋之余有着些遗憾,那就是每年的五月,当一树白白的栀子花又兀自开在我家的竹篱外时,有多么美,就有我们多么的羡慕眼光!
那是一个奶奶的菜园。那颗栀子树是奶奶栽的。
听说,这个小镇的水系很长,连着外面的大世界。也听说,她是国民党军官一位流亡时隐匿的姨太太。她常常是一个人,有着旧上海女人的风姿和神韵,带着淡淡的忧伤。
对这棵栀子树,她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松土、施肥,时时静静地望着树儿抽枝发芽,五月底的花季,晨光中她会伫立树边,凝视那些隔夜绽出的花蕾袅袅地开放,目光珍爱、温暖。在我的记忆里,她从不摘那些白粉粉的栀子花,就那么留着,让她飘走最后一缕香魂。
终于有一日,她看到了竹篱边愣直直的几双眼晴。可能是读懂了女孩的渴望,她温婉地问:你们喜欢栀子花?
是的,是的。妹妹甚至激动得叫起来了。
奶奶迟疑了片刻,回屋拿来一把剪子,一个竹蓝,小心的剪了几朵含苞的花朵递给我们。
给你们戴吧,她配你们。
轻轻地接过花蓝,我们像接过一样珍品,回家用一杯清水养着,让她的幽香从容地缭绕,不敢怠慢。
以后每年的五月末,我们都会收到奶奶递来的一蓝栀子花,姐妹们都小心的呵护着,仿佛她的花魂上承载着很多很多的故事和情感。
旧时光里的栀子花,在我的记忆里年年绽放。那些花、那些景、那些人、那些事,如烟云已过,回忆却很温暖……
一
其实,在南方湖州长大的孩子,打小很少看见栀子花树,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儿时八、九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去舅爷家走亲戚,舅爷离我们家几十公里,走了近乎一整天泥路的小女孩,劳顿把一份新奇和欣喜折腾得只想哭涕,我牵着妈妈的手,深一脚低一脚地走着,终于在向晚时分到达村庄。
记忆中,夕阳下的村庄很美。夏日的微风拂着田畴,禾苗轻轻荡着波浪,青山绿水里,袅袅炊烟从暮霭中升起,一份宁静和温暖让远涉的我有了归依,终于又孩子脸的笑了。
绕过长长的竹篱,我们跨进了舅爷的小院,我被一种从没看过的景致吸引,整整洁洁的庭院里,一栋四间的茅草平房,西边一座低矮的墙上爬满一架嫣红红的蔷薇花。庭院的东边,有一棵开满白色花朵的参天大树,这棵华冠丰荗的大树就是栀子花树。夕阳的金辉照在这个开满鲜花的庭院,花儿的清香幽幽飘来,我仿佛不是走入一个乡野之气的农舍,而是来到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被一种清雅、脱俗的气息围绕。
妈妈曾告诉我,外婆、舅爷的父亲曾是清朝的秀才,那份雅致遗落下来,我想是很自然的。
我很喜欢那个庭院,那棵开满栀子花的大树,很多年后,我记不清在那个庭院里很多的碎事,但清楚的记得,每天清晨我会早早的起床,站在这颗大树下仰着头,看栀子花在夏日的晨露里低眉浅笑,看她们捂着蕾儿白洁洁的开,开出芳香的味道。
二
江水、小镇。白墙黑瓦、青石板路……
这是我的故乡。在青葱的岁月我再次邂遇栀子花。
也许是女孩子爱花做梦的时季,姐妹们总爱在自家的菜园里栽种很多的花草。当缤纷的花们次第开放,兴奋之余有着些遗憾,那就是每年的五月,当一树白白的栀子花又兀自开在我家的竹篱外时,有多么美,就有我们多么的羡慕眼光!
那是一个奶奶的菜园。那颗栀子树是奶奶栽的。
听说,这个小镇的水系很长,连着外面的大世界。也听说,她是国民党军官一位流亡时隐匿的姨太太。她常常是一个人,有着旧上海女人的风姿和神韵,带着淡淡的忧伤。
对这棵栀子树,她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松土、施肥,时时静静地望着树儿抽枝发芽,五月底的花季,晨光中她会伫立树边,凝视那些隔夜绽出的花蕾袅袅地开放,目光珍爱、温暖。在我的记忆里,她从不摘那些白粉粉的栀子花,就那么留着,让她飘走最后一缕香魂。
终于有一日,她看到了竹篱边愣直直的几双眼晴。可能是读懂了女孩的渴望,她温婉地问:你们喜欢栀子花?
是的,是的。妹妹甚至激动得叫起来了。
奶奶迟疑了片刻,回屋拿来一把剪子,一个竹蓝,小心的剪了几朵含苞的花朵递给我们。
给你们戴吧,她配你们。
轻轻地接过花蓝,我们像接过一样珍品,回家用一杯清水养着,让她的幽香从容地缭绕,不敢怠慢。
以后每年的五月末,我们都会收到奶奶递来的一蓝栀子花,姐妹们都小心的呵护着,仿佛她的花魂上承载着很多很多的故事和情感。
旧时光里的栀子花,在我的记忆里年年绽放。那些花、那些景、那些人、那些事,如烟云已过,回忆却很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