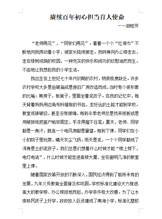今年超山梅花节期间,去超山赏梅,使我联想到了王安石先生的诗【 梅
若水分享
1147
妈妈的双手抚过我的脸颊,温暖的手心贴着我裸露在被子外面的清凉脸颊,肌肤的触摸中,是一种轻轻的硬硌感。我紧闭的双眼微微地睁开,看到妈妈坐于床沿边,苍老的双手轻轻抚过我的脸,将披散在我脸上的发丝拂开,然后将手心抚在我的额际。片刻后,对坐在旁边的爸爸说:没有发烧。后又为我紧了紧被子叹息着离去。
那时,我正头痛欲裂,紧闭着双眼,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与叹息。那份疼痛感里,依稀是妈妈的双手,轻抚的温暖的双手,苍老斑斑,带着一块块的趼子。感触的硌痛直接的便将我引到那之前的瞬间。
仿似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浑不知身在何处,迷离的意识好似漂荡在一片浮浮沉沉的大海上,又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荒原。微微睁开的眼,伴随着渐渐潜进身体里的意识,迷朦中,是爸爸撑扶着我的双手,幻影憧憧的,很努力的让自己醒过来。便清醒的认知到是在床上,撑扶在虚脱的身体上的是爸爸那双苍老稳健的手。手上无一块稍滑适舒服的肌肤。拇指上,虎口上裂开的缝隙贴着一块块新旧不一的胶布,掌背青筋鼓鼓,苍褐遒劲的向手臂深处蜿蜒,掌心是粗硬的趼皮,指节处支开的厚趼开裂有如一朵朵花儿。整个的一双手,苍老的如绽开着一束趼花。那些经年累月的手上的创伤与厚趼只能算是一层硬硬的皮了,不再有疼痛感,拂过细嫩的物体时总有一种唰唰簌簌的声音响起。
那一刻,那迷离的恍惚中,我从一种无力无觉中最先感知的便是那布满厚厚的硬趼的硌肌感。我迅速地闭上自己才清醒过来微启的双眸,任其僵尸般地躺在床上。然后感受着妈妈担忧的抚摸,同样的一双布满了厚厚硬趼的双手,却较之爸爸的双手圆润而温暖。当双手轻轻地抚摸在脸颊与额际之时,泪从眼角潸然而落,滑在脸颊上,触及妈妈的双手。妈妈以为是我身体难受,轻轻地无声的拭擦而过。在她轻轻叹息着转身而去时,我将双眸缩在被子里,用被角试擦着。
也许,不是从那冥幽中清醒过来,我不会那么激凌凌地感触到那两双手的质地纹理。怅然的那么一瞬间里,我的意识一下子拓张而去,是遥远的岁月里,那总是贴着大地的双脚双手,无声的于岁月深处编织着一束束的美丽与忧伤。
我不知道那样一双开满了趼花的双手是需要怎样的代价而致使它虽然面目疮痍,却沉稳厚重。笃实地编织着岁月,稳健地打造着生活,将生命锤炼得锃亮而黝纠。
我记得,小时,冬天里看着爸爸用剪刀将脚跟处厚厚的硬趼剪开,剪下来,得用着很大的力才能剪得下。那时,我问爸爸:疼吗?爸爸说不疼。脚跟处的裂口开得很大,有时甚而渗着鲜红的血丝,在寒冷的天气里凝结。哑然中,心似也感到微微的疼痛。然后看着爸爸在炭火旁弯腰用胶布贴着手指上的伤口。那双手,那双开满了趼花的手,参差斑驳,裂纹纵横。我不知这样的一双手与一双脚是经过怎样的经年累月而致使那么硬冷苍老。
后来,我看到自己手上生出的的趼时,在怔愣中拿着剪刀来剪,似乎真的感知不到疼痛,但那些趼子在漫长年月里却是由一次次的疼痛而累积形成的。那些渗血的裂纹更不用说在冬天的刺寒中产生的疼痛了,当疼痛消失后,便凝成一个个坚实的硬趼。不再惧于疼痛,任何沉重或是坚硬的东西皆不再对手脚肌肉产生一种压迫感。可是,每每看着那样的一双手脚却让人不忍触目,那份疼痛便不由自主的遍布全身,在心尖微微的跳动。
记忆里,爸爸的双脚脚背隆得很高,脚跟裂满了疮痕,一般的鞋子总是很难穿进去,袜子就更不好穿了。冬天里,看着爸爸上山去之前总是赤脚穿着解放鞋,下水田也是赤脚穿着长靴。然后在外一整天,到傍晚时回到家脱下鞋子,脏兮兮的鞋里总是灌满了壤土,鞋底黏腻。一双脚艰难的从鞋中挤脱出来,脚跟那晚间合好的裂纹又裂开了,沾满了草屑泥土,流着血丝,沾结在脚跟处。一双厚而坚硬的脚,在温水里泡上一会儿,将脚跟处的黏结物清理掉,又赤脚穿上了拖鞋。那时,看着爸爸的一双脚,我总是会感到奇怪,问妈妈为什么不给爸爸买袜子,问爸爸为什么不穿袜子,我们就是穿了袜子整双脚都深感冰冷刺痛。妈妈说是爸爸自己不穿,爸爸说他的脚穿不了袜子,厚厚的趼与裂纹在毛毛的袜子里面总是撒扯着袜丝,好不容易穿上了袜子又穿不上鞋,况且爸爸说上山的人穿什么袜子呢。于是,那双脚便经年累月这样在风霜雨露里侵蚀着,直至如今整双脚被厚厚的硬趼与裂纹所包裹。
那双手呢,自是在生活中,年年月月的伺俸于各种硬物,重物,锐物,冷热之物,更是在山间田间地头如脚般的与风霜相携相挽了。任何时候任何时节赤手劳作,搬运着。趼花便似一束幽幽开在岁月深处的花朵,从初春的花骨朵到春末的花蕾再到夏初的花儿,最后在夏秋之节成为一束别样地悬挂在生命枝头的花束。随着朔风的吹来,苍老而僵硬,色泽幽深苍褐,血脉膨胀,遒劲鼓鼓地透支着最后的生命力。昂首着的花芯,在雨露中吮吸采纳,汲取着天地最后的精气。
也许,这是一朵生命力维持最为弥久的花儿,也是一束开得最为灿烂而嫣红的花儿。它的疼痛只有血脉相承的绿叶与枝杆相知,而扎根在土地中的根须总是宽厚而慈爱的输送着营养水分,只想开在它枝头的花儿能够维持得经久些。它的欢悦只有采蜜的蜂儿,恋花的蝶儿知之,震动的双翅是一种倾情的恋慕与眷喜,只想花儿能够陪伴得持久些。
可是,这样的一朵花终究是凌空而开的,终究也如自然中所有的花儿般会凋零,会枯谢。那时,我希望我能双手轻轻地捧住从它枝头流下的泪与血,颤微微地接住那抖动在风里的最后花瓣儿。用我手心里的温暖轻抚那束苍凉的花儿,抚平那些岁月里浸染的忧伤与疼痛。
以前,我不知道趼花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之美。我总以为那是一种人生的沉陷,生活的重压,生命的疼痛。而今,倏然的,我深知那是一种生活的沉淀,心灵的醇笃,自然界的艺术之花。双脚稳厚地踏于大地,双手温实地抚于自然。生活的面目便在那双脚与那双手中被轻轻的捻制铸造。人生的道路也在那双脚与那双手中被延伸拓开。
手与脚的方向指引着生命的趼花,在浑厚的眼眸里点点的绽放,孤独而坚韧。
那时,我正头痛欲裂,紧闭着双眼,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与叹息。那份疼痛感里,依稀是妈妈的双手,轻抚的温暖的双手,苍老斑斑,带着一块块的趼子。感触的硌痛直接的便将我引到那之前的瞬间。
仿似从千年的沉睡中醒来,浑不知身在何处,迷离的意识好似漂荡在一片浮浮沉沉的大海上,又若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荒原。微微睁开的眼,伴随着渐渐潜进身体里的意识,迷朦中,是爸爸撑扶着我的双手,幻影憧憧的,很努力的让自己醒过来。便清醒的认知到是在床上,撑扶在虚脱的身体上的是爸爸那双苍老稳健的手。手上无一块稍滑适舒服的肌肤。拇指上,虎口上裂开的缝隙贴着一块块新旧不一的胶布,掌背青筋鼓鼓,苍褐遒劲的向手臂深处蜿蜒,掌心是粗硬的趼皮,指节处支开的厚趼开裂有如一朵朵花儿。整个的一双手,苍老的如绽开着一束趼花。那些经年累月的手上的创伤与厚趼只能算是一层硬硬的皮了,不再有疼痛感,拂过细嫩的物体时总有一种唰唰簌簌的声音响起。
那一刻,那迷离的恍惚中,我从一种无力无觉中最先感知的便是那布满厚厚的硬趼的硌肌感。我迅速地闭上自己才清醒过来微启的双眸,任其僵尸般地躺在床上。然后感受着妈妈担忧的抚摸,同样的一双布满了厚厚硬趼的双手,却较之爸爸的双手圆润而温暖。当双手轻轻地抚摸在脸颊与额际之时,泪从眼角潸然而落,滑在脸颊上,触及妈妈的双手。妈妈以为是我身体难受,轻轻地无声的拭擦而过。在她轻轻叹息着转身而去时,我将双眸缩在被子里,用被角试擦着。
也许,不是从那冥幽中清醒过来,我不会那么激凌凌地感触到那两双手的质地纹理。怅然的那么一瞬间里,我的意识一下子拓张而去,是遥远的岁月里,那总是贴着大地的双脚双手,无声的于岁月深处编织着一束束的美丽与忧伤。
我不知道那样一双开满了趼花的双手是需要怎样的代价而致使它虽然面目疮痍,却沉稳厚重。笃实地编织着岁月,稳健地打造着生活,将生命锤炼得锃亮而黝纠。
我记得,小时,冬天里看着爸爸用剪刀将脚跟处厚厚的硬趼剪开,剪下来,得用着很大的力才能剪得下。那时,我问爸爸:疼吗?爸爸说不疼。脚跟处的裂口开得很大,有时甚而渗着鲜红的血丝,在寒冷的天气里凝结。哑然中,心似也感到微微的疼痛。然后看着爸爸在炭火旁弯腰用胶布贴着手指上的伤口。那双手,那双开满了趼花的手,参差斑驳,裂纹纵横。我不知这样的一双手与一双脚是经过怎样的经年累月而致使那么硬冷苍老。
后来,我看到自己手上生出的的趼时,在怔愣中拿着剪刀来剪,似乎真的感知不到疼痛,但那些趼子在漫长年月里却是由一次次的疼痛而累积形成的。那些渗血的裂纹更不用说在冬天的刺寒中产生的疼痛了,当疼痛消失后,便凝成一个个坚实的硬趼。不再惧于疼痛,任何沉重或是坚硬的东西皆不再对手脚肌肉产生一种压迫感。可是,每每看着那样的一双手脚却让人不忍触目,那份疼痛便不由自主的遍布全身,在心尖微微的跳动。
记忆里,爸爸的双脚脚背隆得很高,脚跟裂满了疮痕,一般的鞋子总是很难穿进去,袜子就更不好穿了。冬天里,看着爸爸上山去之前总是赤脚穿着解放鞋,下水田也是赤脚穿着长靴。然后在外一整天,到傍晚时回到家脱下鞋子,脏兮兮的鞋里总是灌满了壤土,鞋底黏腻。一双脚艰难的从鞋中挤脱出来,脚跟那晚间合好的裂纹又裂开了,沾满了草屑泥土,流着血丝,沾结在脚跟处。一双厚而坚硬的脚,在温水里泡上一会儿,将脚跟处的黏结物清理掉,又赤脚穿上了拖鞋。那时,看着爸爸的一双脚,我总是会感到奇怪,问妈妈为什么不给爸爸买袜子,问爸爸为什么不穿袜子,我们就是穿了袜子整双脚都深感冰冷刺痛。妈妈说是爸爸自己不穿,爸爸说他的脚穿不了袜子,厚厚的趼与裂纹在毛毛的袜子里面总是撒扯着袜丝,好不容易穿上了袜子又穿不上鞋,况且爸爸说上山的人穿什么袜子呢。于是,那双脚便经年累月这样在风霜雨露里侵蚀着,直至如今整双脚被厚厚的硬趼与裂纹所包裹。
那双手呢,自是在生活中,年年月月的伺俸于各种硬物,重物,锐物,冷热之物,更是在山间田间地头如脚般的与风霜相携相挽了。任何时候任何时节赤手劳作,搬运着。趼花便似一束幽幽开在岁月深处的花朵,从初春的花骨朵到春末的花蕾再到夏初的花儿,最后在夏秋之节成为一束别样地悬挂在生命枝头的花束。随着朔风的吹来,苍老而僵硬,色泽幽深苍褐,血脉膨胀,遒劲鼓鼓地透支着最后的生命力。昂首着的花芯,在雨露中吮吸采纳,汲取着天地最后的精气。
也许,这是一朵生命力维持最为弥久的花儿,也是一束开得最为灿烂而嫣红的花儿。它的疼痛只有血脉相承的绿叶与枝杆相知,而扎根在土地中的根须总是宽厚而慈爱的输送着营养水分,只想开在它枝头的花儿能够维持得经久些。它的欢悦只有采蜜的蜂儿,恋花的蝶儿知之,震动的双翅是一种倾情的恋慕与眷喜,只想花儿能够陪伴得持久些。
可是,这样的一朵花终究是凌空而开的,终究也如自然中所有的花儿般会凋零,会枯谢。那时,我希望我能双手轻轻地捧住从它枝头流下的泪与血,颤微微地接住那抖动在风里的最后花瓣儿。用我手心里的温暖轻抚那束苍凉的花儿,抚平那些岁月里浸染的忧伤与疼痛。
以前,我不知道趼花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之美。我总以为那是一种人生的沉陷,生活的重压,生命的疼痛。而今,倏然的,我深知那是一种生活的沉淀,心灵的醇笃,自然界的艺术之花。双脚稳厚地踏于大地,双手温实地抚于自然。生活的面目便在那双脚与那双手中被轻轻的捻制铸造。人生的道路也在那双脚与那双手中被延伸拓开。
手与脚的方向指引着生命的趼花,在浑厚的眼眸里点点的绽放,孤独而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