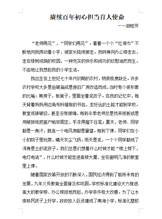粉墙黛瓦何处寻
若水分享
1147
一、
几天前,在政协工作的老王与我约定,周末我们一同到乡下,去拍老房子。一个闲官加上我这个闲人,居然动起崇高的念头,要把那些还残存的凝固的文化,摄入相机,留给后人。
我们的黑色奥迪在平坦、笔直的柏油路上奔驶,路边上一排排的香樟树、一盏盏的路灯,整齐站立着,像是在等候着什么。
这座太湖边上的小城,这些年像是使足了化肥的稻苗,一个劲的疯长。那些由青石板铺成,由石拱桥、小木桥衔接在一起的小街、小巷,在推土机和压路机的轰鸣声里,连同伴随它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高大梧桐树、老榆树,顷刻间就不见了,变成了无遮无拦的宽阔大马路。路两边原本秀气、低矮的木板房、大屋顶的两、三层的小楼房,先是被人在雪白的粉墙上用朱笔写上一个大大的拆字,然后就看见有农民工兄弟挥舞着大锤,在房顶上展示力量,再后来,就像是变魔术一般在原地长出了钢筋水泥的大树——二十层、三十层的大厦和楼房。十多年的光景,它们已经沿路长成了一片森林,几乎遮盖了天空,白天把阳光撕扯成布条,夜里索性赶走了星星和月亮。
小街小巷不见了,也就不见了那晶莹弯曲的小河,小河上悠闲的小船;不见了那爬满月季、蔷薇的篱笆墙;不见了从小楼木窗里伸出来的晾衣杆和举着晾衣杆的姑娘。小街小巷不见了,清晨也就听不到了家家户户,开门开窗的吱呀声响,也就听不到晚间小河上桨橹的咿呀声响,听不到了小商小贩的叫卖市声、姑娘们银铃般的笑声……公路就像是一个黑色杀手,它延伸到哪里,就把哪里上千年的农耕文明谋杀在光天化日之下。
太阳羞涩的从半透明的天空中露出昏黄色的脑袋,醉眼惺忪的向我们的车窗内张望。这些年工厂废气、汽车尾气、燃烧烟气,加上土地荒漠化造成的沙尘暴,让我们重新结识了古书上的生僻字“霾”。原本山明水秀的小城,变得像塑料布里看天——混混沌沌。老王插一只光盘进光驱,我们的车子里,立刻传出一个深情的吴语女声:“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我大声的骂老王:“你无聊啊,一湖的蓝藻,美个屁。”老王不理我,眨眨眼对我笑。
车子驶进城区,马路立刻变窄了。我们很快就被挤进了人流、车流中,滚动的车轮慢了下来,一节一节的往前蹭,仿佛是在跟路上的行人一起步行。蹭的久了,觉得实在无聊,打开车窗,耳朵里立刻传进噪杂喧嚣的喊声、笑声、叫骂声、商店里传出的高分贝喇叭声,还有警察沙哑的叱责声。
在这个初春的上午,满眼是包裹在西装、夹克、羽绒服、风衣和长裙中的男男女女,老头子把自己围裹的像是狗熊,年轻姑娘却把自己装扮成美丽“冻人”。提菜篮的大多步履蹒跚,挎包、背包的大多疾步匆匆。从车窗向外平视,映入眼球的是长发、短发、光头、帽子、脸和眼睛。我第一次发现,小城人的服装是那样的五花八门、绚丽多彩;小城人的表情是那样的丰富多姿、滑稽生动。眼光从人们的头顶掠过,是街边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告示板、广告牌、商店招牌和霓虹灯。它们的后边是拥挤在一起的饭庄、酒楼、茶馆、商店……把眼睛往上抬抬,是灰蒙蒙的天空。
我感到有些压抑,关上车窗,向前望去,满眼都是车子,有公交车、出租车、卡车、轿车、工程车、面包车,还有吵得人心烦的救护车和警车。原本只有自行车和手推车的小城,自从小街、小巷变成了大马路,仿佛一夜间,就变成了甲壳虫的世界。这个鬼迷心窍的世界,不知什么时候玩起了围追堵截的游戏,到处都堵。小路堵,大路堵,地下道堵、高架桥堵,处处都堵,人心更堵。
桃红柳绿,粉墙黛瓦;斜风细雨,深巷曲弄;小桥流水,枕河人家……原先的小城是那么的娴静、秀丽。拿一把蒲扇,斜倚在美人靠上,听那吴腔吴韵的吴歌;一把紫砂壶,三两个茶盏,闲扯那天南海北事,摆起城里乡下的乌龙阵;从小河里提一桶清水,河埠头上放下木盆,挥起棒槌将衣物轻轻敲打;拖拉着木屐,敲打着青石板,沿着河岸,在那小街店肆前悠闲的溜达……不过十年功夫,这些往昔慢节奏的闲适生活,随同小城现代化的步伐,不知不觉的就走掉了。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这座江南小城里,路很窄、夹弄仄仄,庭院深深,没有高速路,没有高架桥,也没有宽阔的大马路,满眼是曲曲弯弯的小径,歪歪扭扭的小河,城里人骑着自行车,乡下人摇橹驾着小船。没有喧嚣,没有拥堵,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一切都是那样悠闲自然。外人走进小城,看到的是一派素雅婉约的风情、清丽安逸的精致。就这么十多年的时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汗水、智慧和大把的金钱,把一个幽静的小城,弄成了一个处处喧嚣、路路拥堵、人人烦躁的钢筋水泥的垃圾场,灵魂无家可归的精神废墟。面对着由现代化演绎的悖论,我常常问官员、问专家、问自己、问苍天:难道小城的现代化一定要断续历史的文脉,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进程就不能共生共荣吗?建设与破坏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
一百多年前,小城刻印的《县城图》中所标识的“巷”,如今早被“大道”、“大街”取代,没了踪迹。老人们嘴里的里、巷、弄、坊,在辞典里也渐渐成了生僻词。农耕文明时代,每一次改朝换代几乎都有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不管多么酷烈的战争,总会留下一地废墟。而小城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那些代表过去年代文明的老房子、老建筑却没有留下一点踪影。这场由无知的官员们指挥的,现代化对古老文明的战争,就像一个只吞吃,不排泄的怪兽。
我们的车子在拥堵中慢慢向前磨蹭。忽然,我看到一个老人伫立在高架桥头,晨风吹动他满头雪白的银丝,两眼仰望着眼前的高楼大厦。他是在寻找从前的时光吧,从前这里是一条悠长的小巷,他或许是在寻找记忆里小巷的去向。我看见老人举起了双手,手中端起一架照相机,原来他是来拍照的。顺着他照相机瞄准的方向,我看到前边的高楼边上,还有几座两层小楼,那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啊。粉白的墙上,是一个个朱红的、血色的、大大的“拆”字。老人不断变换着角度,拍了一张又一张。我想,他是在摄取即将失去的家园,他在拍摄这座小城曾经的昨天和前天,他在拍摄留给儿孙的回忆和永恒。
看着老人的举动,我心中升起莫名的感动。
二、
这是座据说有3200年历史的江南小城。商末周太王的两个儿子,泰伯、仲雍千里奔吴,带来中原文明,于是沼泽中的土著从树巢上下来,住进最原始的干栏式建筑。我猜想,当年句吴国第一任国王泰伯的王宫,很可能就是几间茅草棚。历经数千年风风雨雨的洗礼,沧海桑田的变迁,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的传承、不断的改进,形成了今天江南民居独特的风格。有人说,典型的中国民居,就是北方胡同里的四合院、江南临水雨巷里的大屋顶小楼。这话虽然有些偏颇,但大致上说来,却也距离事实不远。
建筑是凝固的史诗,江南民居是站立着的乐章。这些历经历史风雨的老房子,一砖一瓦里,都展现着它诞生年代的历史风情、哲学思想、生活情趣、民俗民风;一朝一进里,都反映着过去时代的艺术水平、审美思想、技术水准、构建技巧;一听一堂里,无不彰显房屋主人的历史风貌、社会地位、家庭身份、价值取向。
走进幽幽雨巷,踏入深深庭院,暮然回首,你会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在历史中穿越。那些亭台楼阁,或许有盛唐时的小姐曾在上面张望,“梳洗罢,独倚望江楼”。那些馆院台榭,或许有宋代的怨妇,月下笙歌,哭叹“人比黄花瘦”。手握招摇旗,青石板上走着明代的算命瞎子。一桌一椅一块响木,晚清的茶馆里,竖着眉飞色舞的说书先生。在民初的历史空间里,走来走村串户的挑担货郎,修锅补碗的工匠师傅;村头土庙里,有修行的和尚、道士、尼姑;村尾的大树下,有歇晌的农人、过路客、牧童;厅堂和灶披间里,忙绿着村妇和村姑……古老的江南民居,每一条小巷都演绎着沧桑传说,每一座小桥都记载着人间传奇,每一栋小楼都曾经发生过悲欢离合的故事。
只是,历史就像是个有着自己周期律的圆,在岁月的丰腴和消瘦中,转过一圈后,还会走向闭环的原点。她从无中生有,又从有中变无。如今,小城的那些维系着“过去”的老房子,大多在迈向现代化的狂热大拆大建中,不见了踪影。剩下的断垣残壁,也被圈进景区、公园,做成了传统文化的标本。它们最终成了小城遮羞布后的私处,如同谁要一亲妓女的芳泽,必须掏出买笑钱。
寻找老房子,城里无奈。只能出城去,寻访那些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古镇。
我们的车子,停在了此行的第一站,玉祁镇。玉祁古镇,原本是已经湮没的古芙蓉湖中的一块高地,位于无锡、常州、江阴的交界处,迄今有4000多年历史,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出生在这座名人辈出,人文荟萃的古镇。
车子刚在路边停稳,就看到了专程来迎接我们的老张,他是当地电视台的负责人。老张笑吟吟的拉着我们的手,一同向镇里走去。
与城里一样的大马路、一样的高架桥、一样的火柴盒般方方正正、呆头呆脑的高楼,江南高速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将城与镇衔接的天衣无缝。这是古镇吗,这里能寻到传统的老房子?我停下脚步,四处张望。老张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依旧笑吟吟地扯着我的衣袖,带领我们绕过高楼,拐进一条小路,又弯进一条小弄堂。老张是当代人,一边带着我们七拐八弯的在小街小巷里转圈,一边与那些酱油铺、小茶馆、麻将屋、烟酒店的小老板们寒暄、打招呼。
渐渐的,我的眼前亮起来了。木头的电线杆、潺潺流动的小河、粉白的马头墙、女儿墙、雕花的青砖门楼、雅致的六角、八角花窗,还有顶在山墙上的砖砌烟囱。没想到哈,在这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还真的隐藏着一座古村落,整整一条街的古巷。我跟在老王的身后,兴奋的来不及言语,就端起相机,咔嚓、咔嚓的拍起来。
拍过一条街巷,再举起相机的时候,我傻眼了。哪里还有什么江南老房子,我眼前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江南最丑陋的灰色水泥楼房,它们长长方方、呆头呆脑的戳在那里。再放眼望去,还有一些“古为今用”的老屋,后面的居室是旧房,前边的厅堂外墙却帖上了马赛克。电话线、电视线、电脑线,像是蛛网一样盘踞外墙,原本雅致的花窗下,却蹲踞着怪兽般的空调外机。再回头看自己刚刚拍过的那些临河民居,墙上大多朱笔写着大大的“拆”字。这些朱红的大字,很快在我的眼里,幻化成滴血的伤口。
当我站在一座小桥桥头的时候,彻底傻眼了。这座曾经车水马龙的古桥,已经有一半被埋进了陆地,还有一半勉强留在水上。它身下的河也就成了一条不再流动的断头河。一河死水,呈现的是酱黄的颜色,散发出一阵浓一阵淡的腥臭味。这腥臭里,还混着一丝酒糟香。河岸的东侧,是一座破旧的酒厂。陪同我们的老张说:儿时这里是一河碧波,河岸上是淘米洗菜的村姑,还有围坐一起绣花聊天的老阿婆,孩子们在水里戏水,河船上是男人们运往城里的菜蔬瓜果……这一切现在都没了,乡镇企业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小河污染了,河两岸几乎成了垃圾场。
唉,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夜以继日地向现代化奔跑,却在文明中迷失了方向。工业化使人人都成了机械上的一颗油腻的螺丝钉,人性丧失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被无情地割裂了。人,变成了一串号码、一张证书。当金钱成了衡量人们成功与否的标志时,金钱的商业属性,就使得人们再也找不到稳定而有效的生活信念。以往理性主义的文明,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价值体系、精神家园,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轰然崩溃了。
“你们是来拆房子的吗?”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被一群老阿婆给围起来了。“不是的。我们不是拆房子的。”“不拆房子,干嘛要走街穿巷的拍照?”阿婆们追问。“你们给的钱太少了,太黑心了。”阿婆们愤愤地说。
这时,我才知道我们遇到麻烦了。好在老张来了,领我们突出了误会的重围。
吃过午饭,老张问我们:“还有一个去处,你们要不要看,是最近拆了旧房子,重建的一组仿古建筑。”
“那就不去了,拆了真的,盖些个假的,有什么意思啊。”我们谢绝了老张的好意。
我们来拍老房子,是要来拍它承载的历史与文化,不是来拍个美丽的外壳。
三
告别老张,我们发动车子,奔向下一个目标:小城东南边的鸿山镇。这是一座号称:“泰伯故里、至德名邦、文化名镇、院士之乡”、与天堂之城苏州相接的古镇。
老张告诉我们,那个古镇上有条老街叫做西仓,那些老房子你们或许感兴趣。那好吧,就去哪。我们驱车直奔西仓。可惜,我们并不认识西仓,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就是车上的导航仪也没有标注。鼻子下边有张嘴,路在嘴上,我们一路问下去。
车到一个山庄,门前站着个五十多岁的老保安。“师傅,知道西仓老街吗?”“不知道,没听说过。”“现在还有什么老街啊”。我听到了保安的小声嘀咕。绕过一个弯,看见桃林边蹲着一位姑娘,我上前问:“毛乌头,西仓老街怎么走?”“什么西仓老街啊,没听说过。”姑娘笑答。“就是有解放前老房子的那个村子。”我对她解释。“哪里还有什么老房子啊。这里是开发区,老房子早就扒光了。”姑娘的回答让我失望。
我们心有不甘,继续驱车在鸿山镇上兜圈子。车子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我看见一位年过六旬的保洁工。“老师傅,问个讯。西仓老街怎么走啊?”我打开车窗大声的问。“西仓老街哈,你说得是满街破房子的那个村子吗?顺右边的大道一直开下去,二十分钟车程,看见个警察岗亭,右拐,前边高架桥边上就是。”终于问对了人。我赶紧下车去和老人握手。他说,他就是那个村里的人。
尽管有老人指路,我们还是跑错了方向。江南小城的路,很多都是填埋了的河道。不像北方城市那样正南正北的,都是些七扭八拐的盘陀路,很容易迷失方向。也是歪打正着,我们稀里糊涂的开到了钱穆、钱伟长故居。
钱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宗儒”,钱伟长被誉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这对叔侄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不过,这故居,有经验的人从鲜亮的砖瓦上一看,就知道是这几年拆旧建新的产物。上世纪一把大火将钱氏老屋烧成废墟,残留部分不足二十平米。
故居就在公路边上,老远就能看见公路上的招牌:怀海义庄,钱氏故居。带着对两位钱氏伟人的崇敬,我们绕庄一周。这组仿古建筑,青砖黛瓦、楼台水榭,颇具江南水乡风情。故居门前是一条叫“啸傲泾”的小河,河水潺潺,在午后的阳光下,闪动着粼光,只是河边上的钢筋水泥围栏有点画蛇添足,大煞风景。故居的大门边上,开了一扇六角花窗,是故居售票处。从这个窗口里飘出的商业味道,让人多少有些不舒服。
“这新修的‘古’建筑没什么看的,我们还是赶路吧。”我说。“急什么?再仔细看看,说不定五百年后,这假的就成了真的,成了真的文物。”老王的调侃,惹得我们周围的人都笑了。
赶到西仓老街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正如老保洁工所说,这个村子满眼都是破房子。顺着一条河边逼仄的小径,我们走进村口。一位老者正在河塘边上杀鱼。望着满眼的枯藤、死树、圯墙、破屋,我有些疑惑,大声的问老者:“师傅,这里是西仓老街吗?”“是啊”杀鱼的老者抬头回答。“怎么这么破啊?”我问。“唉,年轻人都去城里上班了,住城里不回来了,就剩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了。有些人家老头子、老太婆死了,房子也没人管了,能不破吗?”老人回答我的时候,头也没抬。
走上一座小桥,我们的眼前忽然就出现美丽的亮光。从桥上望下去,两岸夹河的是古老秀丽的民居。这些都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啊。粉墙黛瓦与太阳的余晖一起倒映在河面上,黑黢黢的长檐大屋顶、木雕的细格花窗、伸向水面的水阁子、青石台阶的水码头、河埠头,还有一间是正在冒烟的老虎灶。年轻时在城里常见的雨巷景观,现在从梦中,又重现眼前。幽幽曲径收放自如、开阖有度,于不经意间透出唐诗宋词里才有的情趣,岁月从老房子雕花的窗前流过,杏花雨里曾有多少咿呀橹声,留下历史的脚步。
我和老王一阵狂拍,说不出心中有多么兴奋。
走下小桥,走进老街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小桥上的风景,不过是由光线和水波幻化的梦境。这些沿河老房子临街的一面,都已经非常的破旧。有些砖雕装饰的门楼已经掉了半边,古老的门板也被虫子蛀出大大小小的洞眼,外墙的青砖被风雨侵蚀的酥软,手一抹就会粉尘般飘散。那些曾经的雕花木窗,已经腐烂了,窗框像是骷髅的眼窝。有一幢小楼的外墙已经大部分塌了,只是因为江南民居特有的榫卯木结构,才使整幢房子没有倾圯,像是挂在什么地方的大牲畜的骨架,在风中飘摇。这些没人居住的老房子,夜半三更会不会有鬼唱歌?这个奇怪的念头刚刚涌出脑海,我不禁被自己的胡想吓得一哆嗦。
唉,可怜的江南老房子,就像是旧时上海滩上还不起“印子钱”的女人,同时面临着被人砍杀和被逼自杀的两种厄运,而且无路可逃。
在村子的西边,我们发现了一座独立的庭院,这是一组保护的还比较好的老房子。整组庭院,前门是砖雕门楼,本色的木门上,斜挂着几棵干枯的蒲草和两株大蒜。庭院被高大的青砖围墙环绕,庭院的后边围着篱笆,里边种着青菜、蒜苗和韭菜。篱笆墙外两侧种着几丛翠竹,枝条上挂着破布条和废旧的塑料袋。庭院西侧的便门连着一条碎石小径,通向一条小河的水码头。当地村民告诉我们,这里原本是户大户人家,现在住着一个老太太。
围着这所老房子,拍了许多照片之后,老王和我商量,能不能敲开这户人家,到庭院里去看看。我们走到正门前,笃笃笃的敲门,没有动静,再敲,还是没有动静,第三次再敲,里边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门打开一条缝。我走上前去,发现门后顶着一条长条桌子。桌后,立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太,看上去有七旬年纪。“阿婆,我们想进去看看你的房子,这房子有一百年了吧?”我尽量和蔼地问。“不行,我家里没人,你不能进来。”她警惕的回答。“阿婆,我们想拍拍这房子的内部结构,这样的老房子已经不多了。”我说。“这房子一百多年了,破的快坍了,没什么好拍的。”老太太说完,吱呀一声把门关了。
我和老王面面相视,无话可说。
回到村口的时候,我们再次走进村边上的小河。河边上一座破房子门前,一个大约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正在编制渔网。老王问他:“老伯,你这渔网派啥用场啊?”“捉鱼。”“在哪里捉啊。”老头努了努嘴:“就在这条河里。”“这条河里的鱼能吃吗?”老王疑惑的问。“能!”老头回答的很干脆。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我一边放眼向河里望去。河沿上是一堆堆的垃圾,河面上也漂浮着垃圾。河水被污染成了酱汤色,水面静静的,显然这是一条不流动的死河。这样的河里居然还有鱼,这河里的鱼还能吃?我不由的感叹中国鱼和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太阳已经靠上了远山,把山顶上的晚霞照成了一团熔金。在高架路上回望西仓老街,暮霭沉沉中,黄昏的夕阳光照,让它的粉墙黛瓦和黑色大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又幻化出秀丽的身影。我不由的想,如果政府肯出些钱,对它进行修旧如旧的改造,它一定会成为一个保留了江南民居风情的好景观。那时,一定会游人如织的。
古老的江南民居,这承担了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建筑,这延续着历史文脉的活化石。一些被野蛮的拆毁了,一些在自然地坍塌。这些由历史创造的财富,都是一次性的,毁坏了便无法再生。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就不能让历史与现代共生共荣?为什么不去珍惜它、保护它。我们的现代化,难道非要让这些承载历史文化的古建筑消失殆尽做代价吗?后来的人会怎么看我们,他们一定会骂我们是阉割历史文化的一代,是揣着文凭和高学历的文盲!
想到这些,我不禁想起著名作者冯骥才先生在《手下留情》一文中的大声疾呼:“现在的关键人物是城市的管理者们。如果他们先觉悟,未来的文明便提前一步来到今天,如果他们还没觉悟呢?我们只有大呼一声:手下留情!为了后代,请留住城市这仅存不多的历史吧!”
下了高架路,斜晖余脉渐渐隐去,小城华灯初上,我们的车子很快就融入了钢筋水泥的森林里。
几天前,在政协工作的老王与我约定,周末我们一同到乡下,去拍老房子。一个闲官加上我这个闲人,居然动起崇高的念头,要把那些还残存的凝固的文化,摄入相机,留给后人。
我们的黑色奥迪在平坦、笔直的柏油路上奔驶,路边上一排排的香樟树、一盏盏的路灯,整齐站立着,像是在等候着什么。
这座太湖边上的小城,这些年像是使足了化肥的稻苗,一个劲的疯长。那些由青石板铺成,由石拱桥、小木桥衔接在一起的小街、小巷,在推土机和压路机的轰鸣声里,连同伴随它们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高大梧桐树、老榆树,顷刻间就不见了,变成了无遮无拦的宽阔大马路。路两边原本秀气、低矮的木板房、大屋顶的两、三层的小楼房,先是被人在雪白的粉墙上用朱笔写上一个大大的拆字,然后就看见有农民工兄弟挥舞着大锤,在房顶上展示力量,再后来,就像是变魔术一般在原地长出了钢筋水泥的大树——二十层、三十层的大厦和楼房。十多年的光景,它们已经沿路长成了一片森林,几乎遮盖了天空,白天把阳光撕扯成布条,夜里索性赶走了星星和月亮。
小街小巷不见了,也就不见了那晶莹弯曲的小河,小河上悠闲的小船;不见了那爬满月季、蔷薇的篱笆墙;不见了从小楼木窗里伸出来的晾衣杆和举着晾衣杆的姑娘。小街小巷不见了,清晨也就听不到了家家户户,开门开窗的吱呀声响,也就听不到晚间小河上桨橹的咿呀声响,听不到了小商小贩的叫卖市声、姑娘们银铃般的笑声……公路就像是一个黑色杀手,它延伸到哪里,就把哪里上千年的农耕文明谋杀在光天化日之下。
太阳羞涩的从半透明的天空中露出昏黄色的脑袋,醉眼惺忪的向我们的车窗内张望。这些年工厂废气、汽车尾气、燃烧烟气,加上土地荒漠化造成的沙尘暴,让我们重新结识了古书上的生僻字“霾”。原本山明水秀的小城,变得像塑料布里看天——混混沌沌。老王插一只光盘进光驱,我们的车子里,立刻传出一个深情的吴语女声:“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我大声的骂老王:“你无聊啊,一湖的蓝藻,美个屁。”老王不理我,眨眨眼对我笑。
车子驶进城区,马路立刻变窄了。我们很快就被挤进了人流、车流中,滚动的车轮慢了下来,一节一节的往前蹭,仿佛是在跟路上的行人一起步行。蹭的久了,觉得实在无聊,打开车窗,耳朵里立刻传进噪杂喧嚣的喊声、笑声、叫骂声、商店里传出的高分贝喇叭声,还有警察沙哑的叱责声。
在这个初春的上午,满眼是包裹在西装、夹克、羽绒服、风衣和长裙中的男男女女,老头子把自己围裹的像是狗熊,年轻姑娘却把自己装扮成美丽“冻人”。提菜篮的大多步履蹒跚,挎包、背包的大多疾步匆匆。从车窗向外平视,映入眼球的是长发、短发、光头、帽子、脸和眼睛。我第一次发现,小城人的服装是那样的五花八门、绚丽多彩;小城人的表情是那样的丰富多姿、滑稽生动。眼光从人们的头顶掠过,是街边上让人眼花缭乱的告示板、广告牌、商店招牌和霓虹灯。它们的后边是拥挤在一起的饭庄、酒楼、茶馆、商店……把眼睛往上抬抬,是灰蒙蒙的天空。
我感到有些压抑,关上车窗,向前望去,满眼都是车子,有公交车、出租车、卡车、轿车、工程车、面包车,还有吵得人心烦的救护车和警车。原本只有自行车和手推车的小城,自从小街、小巷变成了大马路,仿佛一夜间,就变成了甲壳虫的世界。这个鬼迷心窍的世界,不知什么时候玩起了围追堵截的游戏,到处都堵。小路堵,大路堵,地下道堵、高架桥堵,处处都堵,人心更堵。
桃红柳绿,粉墙黛瓦;斜风细雨,深巷曲弄;小桥流水,枕河人家……原先的小城是那么的娴静、秀丽。拿一把蒲扇,斜倚在美人靠上,听那吴腔吴韵的吴歌;一把紫砂壶,三两个茶盏,闲扯那天南海北事,摆起城里乡下的乌龙阵;从小河里提一桶清水,河埠头上放下木盆,挥起棒槌将衣物轻轻敲打;拖拉着木屐,敲打着青石板,沿着河岸,在那小街店肆前悠闲的溜达……不过十年功夫,这些往昔慢节奏的闲适生活,随同小城现代化的步伐,不知不觉的就走掉了。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这座江南小城里,路很窄、夹弄仄仄,庭院深深,没有高速路,没有高架桥,也没有宽阔的大马路,满眼是曲曲弯弯的小径,歪歪扭扭的小河,城里人骑着自行车,乡下人摇橹驾着小船。没有喧嚣,没有拥堵,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一切都是那样悠闲自然。外人走进小城,看到的是一派素雅婉约的风情、清丽安逸的精致。就这么十多年的时光,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汗水、智慧和大把的金钱,把一个幽静的小城,弄成了一个处处喧嚣、路路拥堵、人人烦躁的钢筋水泥的垃圾场,灵魂无家可归的精神废墟。面对着由现代化演绎的悖论,我常常问官员、问专家、问自己、问苍天:难道小城的现代化一定要断续历史的文脉,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进程就不能共生共荣吗?建设与破坏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
一百多年前,小城刻印的《县城图》中所标识的“巷”,如今早被“大道”、“大街”取代,没了踪迹。老人们嘴里的里、巷、弄、坊,在辞典里也渐渐成了生僻词。农耕文明时代,每一次改朝换代几乎都有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不管多么酷烈的战争,总会留下一地废墟。而小城的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推土机的轰鸣,那些代表过去年代文明的老房子、老建筑却没有留下一点踪影。这场由无知的官员们指挥的,现代化对古老文明的战争,就像一个只吞吃,不排泄的怪兽。
我们的车子在拥堵中慢慢向前磨蹭。忽然,我看到一个老人伫立在高架桥头,晨风吹动他满头雪白的银丝,两眼仰望着眼前的高楼大厦。他是在寻找从前的时光吧,从前这里是一条悠长的小巷,他或许是在寻找记忆里小巷的去向。我看见老人举起了双手,手中端起一架照相机,原来他是来拍照的。顺着他照相机瞄准的方向,我看到前边的高楼边上,还有几座两层小楼,那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啊。粉白的墙上,是一个个朱红的、血色的、大大的“拆”字。老人不断变换着角度,拍了一张又一张。我想,他是在摄取即将失去的家园,他在拍摄这座小城曾经的昨天和前天,他在拍摄留给儿孙的回忆和永恒。
看着老人的举动,我心中升起莫名的感动。
二、
这是座据说有3200年历史的江南小城。商末周太王的两个儿子,泰伯、仲雍千里奔吴,带来中原文明,于是沼泽中的土著从树巢上下来,住进最原始的干栏式建筑。我猜想,当年句吴国第一任国王泰伯的王宫,很可能就是几间茅草棚。历经数千年风风雨雨的洗礼,沧海桑田的变迁,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不断的传承、不断的改进,形成了今天江南民居独特的风格。有人说,典型的中国民居,就是北方胡同里的四合院、江南临水雨巷里的大屋顶小楼。这话虽然有些偏颇,但大致上说来,却也距离事实不远。
建筑是凝固的史诗,江南民居是站立着的乐章。这些历经历史风雨的老房子,一砖一瓦里,都展现着它诞生年代的历史风情、哲学思想、生活情趣、民俗民风;一朝一进里,都反映着过去时代的艺术水平、审美思想、技术水准、构建技巧;一听一堂里,无不彰显房屋主人的历史风貌、社会地位、家庭身份、价值取向。
走进幽幽雨巷,踏入深深庭院,暮然回首,你会忽然发现,自己竟然在历史中穿越。那些亭台楼阁,或许有盛唐时的小姐曾在上面张望,“梳洗罢,独倚望江楼”。那些馆院台榭,或许有宋代的怨妇,月下笙歌,哭叹“人比黄花瘦”。手握招摇旗,青石板上走着明代的算命瞎子。一桌一椅一块响木,晚清的茶馆里,竖着眉飞色舞的说书先生。在民初的历史空间里,走来走村串户的挑担货郎,修锅补碗的工匠师傅;村头土庙里,有修行的和尚、道士、尼姑;村尾的大树下,有歇晌的农人、过路客、牧童;厅堂和灶披间里,忙绿着村妇和村姑……古老的江南民居,每一条小巷都演绎着沧桑传说,每一座小桥都记载着人间传奇,每一栋小楼都曾经发生过悲欢离合的故事。
只是,历史就像是个有着自己周期律的圆,在岁月的丰腴和消瘦中,转过一圈后,还会走向闭环的原点。她从无中生有,又从有中变无。如今,小城的那些维系着“过去”的老房子,大多在迈向现代化的狂热大拆大建中,不见了踪影。剩下的断垣残壁,也被圈进景区、公园,做成了传统文化的标本。它们最终成了小城遮羞布后的私处,如同谁要一亲妓女的芳泽,必须掏出买笑钱。
寻找老房子,城里无奈。只能出城去,寻访那些远离城市中心的边缘古镇。
我们的车子,停在了此行的第一站,玉祁镇。玉祁古镇,原本是已经湮没的古芙蓉湖中的一块高地,位于无锡、常州、江阴的交界处,迄今有4000多年历史,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就出生在这座名人辈出,人文荟萃的古镇。
车子刚在路边停稳,就看到了专程来迎接我们的老张,他是当地电视台的负责人。老张笑吟吟的拉着我们的手,一同向镇里走去。
与城里一样的大马路、一样的高架桥、一样的火柴盒般方方正正、呆头呆脑的高楼,江南高速推进的城乡一体化,将城与镇衔接的天衣无缝。这是古镇吗,这里能寻到传统的老房子?我停下脚步,四处张望。老张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依旧笑吟吟地扯着我的衣袖,带领我们绕过高楼,拐进一条小路,又弯进一条小弄堂。老张是当代人,一边带着我们七拐八弯的在小街小巷里转圈,一边与那些酱油铺、小茶馆、麻将屋、烟酒店的小老板们寒暄、打招呼。
渐渐的,我的眼前亮起来了。木头的电线杆、潺潺流动的小河、粉白的马头墙、女儿墙、雕花的青砖门楼、雅致的六角、八角花窗,还有顶在山墙上的砖砌烟囱。没想到哈,在这钢筋水泥的森林里,还真的隐藏着一座古村落,整整一条街的古巷。我跟在老王的身后,兴奋的来不及言语,就端起相机,咔嚓、咔嚓的拍起来。
拍过一条街巷,再举起相机的时候,我傻眼了。哪里还有什么江南老房子,我眼前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江南最丑陋的灰色水泥楼房,它们长长方方、呆头呆脑的戳在那里。再放眼望去,还有一些“古为今用”的老屋,后面的居室是旧房,前边的厅堂外墙却帖上了马赛克。电话线、电视线、电脑线,像是蛛网一样盘踞外墙,原本雅致的花窗下,却蹲踞着怪兽般的空调外机。再回头看自己刚刚拍过的那些临河民居,墙上大多朱笔写着大大的“拆”字。这些朱红的大字,很快在我的眼里,幻化成滴血的伤口。
当我站在一座小桥桥头的时候,彻底傻眼了。这座曾经车水马龙的古桥,已经有一半被埋进了陆地,还有一半勉强留在水上。它身下的河也就成了一条不再流动的断头河。一河死水,呈现的是酱黄的颜色,散发出一阵浓一阵淡的腥臭味。这腥臭里,还混着一丝酒糟香。河岸的东侧,是一座破旧的酒厂。陪同我们的老张说:儿时这里是一河碧波,河岸上是淘米洗菜的村姑,还有围坐一起绣花聊天的老阿婆,孩子们在水里戏水,河船上是男人们运往城里的菜蔬瓜果……这一切现在都没了,乡镇企业的兴起,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小河污染了,河两岸几乎成了垃圾场。
唉,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条件,夜以继日地向现代化奔跑,却在文明中迷失了方向。工业化使人人都成了机械上的一颗油腻的螺丝钉,人性丧失了,人与自然的联系被无情地割裂了。人,变成了一串号码、一张证书。当金钱成了衡量人们成功与否的标志时,金钱的商业属性,就使得人们再也找不到稳定而有效的生活信念。以往理性主义的文明,以及建立在其上的价值体系、精神家园,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轰然崩溃了。
“你们是来拆房子的吗?”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被一群老阿婆给围起来了。“不是的。我们不是拆房子的。”“不拆房子,干嘛要走街穿巷的拍照?”阿婆们追问。“你们给的钱太少了,太黑心了。”阿婆们愤愤地说。
这时,我才知道我们遇到麻烦了。好在老张来了,领我们突出了误会的重围。
吃过午饭,老张问我们:“还有一个去处,你们要不要看,是最近拆了旧房子,重建的一组仿古建筑。”
“那就不去了,拆了真的,盖些个假的,有什么意思啊。”我们谢绝了老张的好意。
我们来拍老房子,是要来拍它承载的历史与文化,不是来拍个美丽的外壳。
三
告别老张,我们发动车子,奔向下一个目标:小城东南边的鸿山镇。这是一座号称:“泰伯故里、至德名邦、文化名镇、院士之乡”、与天堂之城苏州相接的古镇。
老张告诉我们,那个古镇上有条老街叫做西仓,那些老房子你们或许感兴趣。那好吧,就去哪。我们驱车直奔西仓。可惜,我们并不认识西仓,不知道它的确切位置,就是车上的导航仪也没有标注。鼻子下边有张嘴,路在嘴上,我们一路问下去。
车到一个山庄,门前站着个五十多岁的老保安。“师傅,知道西仓老街吗?”“不知道,没听说过。”“现在还有什么老街啊”。我听到了保安的小声嘀咕。绕过一个弯,看见桃林边蹲着一位姑娘,我上前问:“毛乌头,西仓老街怎么走?”“什么西仓老街啊,没听说过。”姑娘笑答。“就是有解放前老房子的那个村子。”我对她解释。“哪里还有什么老房子啊。这里是开发区,老房子早就扒光了。”姑娘的回答让我失望。
我们心有不甘,继续驱车在鸿山镇上兜圈子。车子在十字路口等红灯,我看见一位年过六旬的保洁工。“老师傅,问个讯。西仓老街怎么走啊?”我打开车窗大声的问。“西仓老街哈,你说得是满街破房子的那个村子吗?顺右边的大道一直开下去,二十分钟车程,看见个警察岗亭,右拐,前边高架桥边上就是。”终于问对了人。我赶紧下车去和老人握手。他说,他就是那个村里的人。
尽管有老人指路,我们还是跑错了方向。江南小城的路,很多都是填埋了的河道。不像北方城市那样正南正北的,都是些七扭八拐的盘陀路,很容易迷失方向。也是歪打正着,我们稀里糊涂的开到了钱穆、钱伟长故居。
钱穆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宗儒”,钱伟长被誉为中国近代力学之父。这对叔侄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不过,这故居,有经验的人从鲜亮的砖瓦上一看,就知道是这几年拆旧建新的产物。上世纪一把大火将钱氏老屋烧成废墟,残留部分不足二十平米。
故居就在公路边上,老远就能看见公路上的招牌:怀海义庄,钱氏故居。带着对两位钱氏伟人的崇敬,我们绕庄一周。这组仿古建筑,青砖黛瓦、楼台水榭,颇具江南水乡风情。故居门前是一条叫“啸傲泾”的小河,河水潺潺,在午后的阳光下,闪动着粼光,只是河边上的钢筋水泥围栏有点画蛇添足,大煞风景。故居的大门边上,开了一扇六角花窗,是故居售票处。从这个窗口里飘出的商业味道,让人多少有些不舒服。
“这新修的‘古’建筑没什么看的,我们还是赶路吧。”我说。“急什么?再仔细看看,说不定五百年后,这假的就成了真的,成了真的文物。”老王的调侃,惹得我们周围的人都笑了。
赶到西仓老街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正如老保洁工所说,这个村子满眼都是破房子。顺着一条河边逼仄的小径,我们走进村口。一位老者正在河塘边上杀鱼。望着满眼的枯藤、死树、圯墙、破屋,我有些疑惑,大声的问老者:“师傅,这里是西仓老街吗?”“是啊”杀鱼的老者抬头回答。“怎么这么破啊?”我问。“唉,年轻人都去城里上班了,住城里不回来了,就剩我们这些老头老太了。有些人家老头子、老太婆死了,房子也没人管了,能不破吗?”老人回答我的时候,头也没抬。
走上一座小桥,我们的眼前忽然就出现美丽的亮光。从桥上望下去,两岸夹河的是古老秀丽的民居。这些都是典型的江南民居啊。粉墙黛瓦与太阳的余晖一起倒映在河面上,黑黢黢的长檐大屋顶、木雕的细格花窗、伸向水面的水阁子、青石台阶的水码头、河埠头,还有一间是正在冒烟的老虎灶。年轻时在城里常见的雨巷景观,现在从梦中,又重现眼前。幽幽曲径收放自如、开阖有度,于不经意间透出唐诗宋词里才有的情趣,岁月从老房子雕花的窗前流过,杏花雨里曾有多少咿呀橹声,留下历史的脚步。
我和老王一阵狂拍,说不出心中有多么兴奋。
走下小桥,走进老街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小桥上的风景,不过是由光线和水波幻化的梦境。这些沿河老房子临街的一面,都已经非常的破旧。有些砖雕装饰的门楼已经掉了半边,古老的门板也被虫子蛀出大大小小的洞眼,外墙的青砖被风雨侵蚀的酥软,手一抹就会粉尘般飘散。那些曾经的雕花木窗,已经腐烂了,窗框像是骷髅的眼窝。有一幢小楼的外墙已经大部分塌了,只是因为江南民居特有的榫卯木结构,才使整幢房子没有倾圯,像是挂在什么地方的大牲畜的骨架,在风中飘摇。这些没人居住的老房子,夜半三更会不会有鬼唱歌?这个奇怪的念头刚刚涌出脑海,我不禁被自己的胡想吓得一哆嗦。
唉,可怜的江南老房子,就像是旧时上海滩上还不起“印子钱”的女人,同时面临着被人砍杀和被逼自杀的两种厄运,而且无路可逃。
在村子的西边,我们发现了一座独立的庭院,这是一组保护的还比较好的老房子。整组庭院,前门是砖雕门楼,本色的木门上,斜挂着几棵干枯的蒲草和两株大蒜。庭院被高大的青砖围墙环绕,庭院的后边围着篱笆,里边种着青菜、蒜苗和韭菜。篱笆墙外两侧种着几丛翠竹,枝条上挂着破布条和废旧的塑料袋。庭院西侧的便门连着一条碎石小径,通向一条小河的水码头。当地村民告诉我们,这里原本是户大户人家,现在住着一个老太太。
围着这所老房子,拍了许多照片之后,老王和我商量,能不能敲开这户人家,到庭院里去看看。我们走到正门前,笃笃笃的敲门,没有动静,再敲,还是没有动静,第三次再敲,里边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门打开一条缝。我走上前去,发现门后顶着一条长条桌子。桌后,立着一个矮小的老太太,看上去有七旬年纪。“阿婆,我们想进去看看你的房子,这房子有一百年了吧?”我尽量和蔼地问。“不行,我家里没人,你不能进来。”她警惕的回答。“阿婆,我们想拍拍这房子的内部结构,这样的老房子已经不多了。”我说。“这房子一百多年了,破的快坍了,没什么好拍的。”老太太说完,吱呀一声把门关了。
我和老王面面相视,无话可说。
回到村口的时候,我们再次走进村边上的小河。河边上一座破房子门前,一个大约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正在编制渔网。老王问他:“老伯,你这渔网派啥用场啊?”“捉鱼。”“在哪里捉啊。”老头努了努嘴:“就在这条河里。”“这条河里的鱼能吃吗?”老王疑惑的问。“能!”老头回答的很干脆。一边听着他们的对话,我一边放眼向河里望去。河沿上是一堆堆的垃圾,河面上也漂浮着垃圾。河水被污染成了酱汤色,水面静静的,显然这是一条不流动的死河。这样的河里居然还有鱼,这河里的鱼还能吃?我不由的感叹中国鱼和中国人顽强的生命力。
太阳已经靠上了远山,把山顶上的晚霞照成了一团熔金。在高架路上回望西仓老街,暮霭沉沉中,黄昏的夕阳光照,让它的粉墙黛瓦和黑色大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又幻化出秀丽的身影。我不由的想,如果政府肯出些钱,对它进行修旧如旧的改造,它一定会成为一个保留了江南民居风情的好景观。那时,一定会游人如织的。
古老的江南民居,这承担了数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建筑,这延续着历史文脉的活化石。一些被野蛮的拆毁了,一些在自然地坍塌。这些由历史创造的财富,都是一次性的,毁坏了便无法再生。我们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为什么就不能让历史与现代共生共荣?为什么不去珍惜它、保护它。我们的现代化,难道非要让这些承载历史文化的古建筑消失殆尽做代价吗?后来的人会怎么看我们,他们一定会骂我们是阉割历史文化的一代,是揣着文凭和高学历的文盲!
想到这些,我不禁想起著名作者冯骥才先生在《手下留情》一文中的大声疾呼:“现在的关键人物是城市的管理者们。如果他们先觉悟,未来的文明便提前一步来到今天,如果他们还没觉悟呢?我们只有大呼一声:手下留情!为了后代,请留住城市这仅存不多的历史吧!”
下了高架路,斜晖余脉渐渐隐去,小城华灯初上,我们的车子很快就融入了钢筋水泥的森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