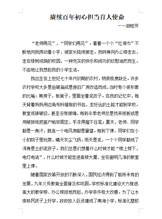小山村的骄傲
若水分享
1147
一
黔东南莽莽苍苍的大山里,仿佛天母随意播撒的种子散落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村寨,它们以山为屏障,以森林为掩护,像一个个处子安详而恬静地躺在大山宽阔的怀抱里,因为大山的滋养与阻隔,她们美丽、穷困而又无知。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的角逐,她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自己的奋斗,也就有了自己的疼痛与骄傲。
四周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山里人根据田土的分布而居,大的村落几百户,小的十几户甚至独家村。我们的村庄有两百多户人家,而且居住非常集中,这对于几个邻近都只有几十户的村落来说,可谓是大地方了。记得小时候流行这样一句儿歌“八柳宰佃猪牛圈,芒岭大队小北京”。没错,我们的村庄就叫芒岭。这句不知何人何时创造,怎样流行起来的俗语是我们小时候的骄傲,每当跟八柳宰佃的孩子们发生矛盾时,我们就故意大声哼唱,甚至不惜时常为此分成两个帮派干上一场。
芒岭,谁也说不清这个名字的由来。我浪漫地猜想,或许是我们的祖先逆江而上,逃难于此时,这座山岭正漫山遍野的开满芒草花,我们的祖先一下子喜欢上了这块美丽而又肥沃的土地,于是安居下来,芒岭因此而得名。村里的老人不同意我的说法,他们说这芒,是芒粑的芒,好多饥荒的年代,到处饿殍遍野,可我们地方从来没有人被饿死,因为我们的山上到处都是蕨菜,而且又懂得将蕨根制作成芒粑,芒岭应是因为这芒粑而得名。
芒粑,就是用蕨根,也叫芒根制作的粑粑。母亲说她七岁的时候就跟外婆上山挖芒根了,而父亲说他们小时候因为吃了太多的芒粑总是全身浮肿。全家人喜欢调侃的一件事是关于五叔的。五叔那个时候还很小,大概四五岁吧,每次叫他吃饭,他就会问,吃什么饭?芒粑。揍你娘,又吃芒粑。嫩声嫩气的骂语让人听着又好笑又心疼。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似乎懂得提起一切植物淀粉的方法。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将红薯、洋芋、南瓜之类做成糕点,比米饭还好吃。没有油,那些难以下咽的菜,根类、茎类、叶子,她都能做成豆腐或者原子,拌上辣椒姜蒜,美味无比。印象最深的,是山上的一种树叶做成的绿色豆腐,味道微苦,还有点涩,但晶莹剔透,十分诱人,母亲说这道菜能够降火利尿,还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鼓励我们多吃。母亲唯独没再做过一次芒粑。虽然我们生长在这个因芒粑而得名的村庄,却没见过芒粑长什么样,出于好奇,我们多次央求妈妈做来偿一偿,可妈妈总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好东西,还做什么芒粑呀,只要想起那个气味我胃就痛。
后来在餐馆里吃到用油精心煎炸过的芋色的芒粑块,那份酥香软糯真是叫人难忘,想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吃到骂娘呢?母亲说,没有油没有盐没有肉掺着炒,你们吃一块试试?母亲不再做芒粑,也许是不愿揭开那痛苦的回忆。但现在时代不同了,那些以前觉得难以下咽的东西,现在摆到桌上却能成为一道独特的美味。而我们现在桌上的许多独特美味,又恰是人们在那些艰苦的年代为免除饥饿而提炼的智慧的结晶。
二
两三里路的距离在城市里比不上一个小区大,但在我们这却坐落着好几个独立的村寨。八柳离我们村大约有三里路程,而中间还隔着大宰佃与小宰佃。八柳座落在一个小山丘上,因而横穿我们寨子中心的马路只是路过他们的山脚,而宰佃距马路还要远一点,在一个山冲里。寨与寨之间,喊一嗓子都能听见,两山的住户,出了门就能相互望见,可是,要从一个寨子走到另一个寨子,要从你家来到我家,却不是那么方便的事,需要在迂回曲折的田埂地埂上绕来绕去才能到达。
在这里,更能让人体会到交通带给人类的骄傲。
我们村庄只因为有了那么一条窄窄的乡间马路,而使我们拥有着巨大的自豪。我们可以骄傲地对那些挑着担子,一摇一晃,艰难地从高山上下来的人大声说:这些山上佬!就好像城里人经过我们身边时,轻蔑地说:这些乡巴佬!山上的姑娘如果能够嫁到沿河一带的村庄,那是多么大的福气与荣耀。如果沿河村庄里的姑娘看上了山上的小伙子,哪怕小伙子人很优秀,也定会遭到家人甚至家族的反对。山里人谁不偿尽了没有路的艰难?谁不想走宽阔的路啊!哪个地方最先拥有宽阔的路,哪个地方的发展就会走在前面。
穿过我们村庄的公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凭人力一铲一锄挖出来的,全是义务工,一个村寨负责几公里,那些座落在山腰上的小村小寨自然没有能力将公路修到屋脚,只能继续过着凭脚力艰难生活的日子。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依旧多是凭借脚力,虽然沿河有几片坝子田,但更多的田土在山上,山里人每天要烧的柴火、换油盐肥料的林木都在山上。不一样的是,有了公路,通往城市的距离就近了,换言之,通往发达与文明的距离就近了。
通公路后,我们村子里第一个买车的人是石三公,比八柳、宰佃、地里有第一辆车的时间都要早。学校里的孩子总是喜欢攀比,比奇事、比发展,七嘴八舌,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响亮。芒岭的孩子们说,我们村有车了,你们村有么?只此一句,别村的孩子就哑口了。
石三公将他的拖拉机开回村子的那天,许多人都来放炮祝贺,宴席从街头一直摆到街尾。从此,村里每天都会响起隆隆的机动车声,村里人的生活也随着这隆隆的声音悄悄地起了变化。秋收的时候,人们用麻袋装好稻谷背到公路旁,然后三公的车子隆隆隆就拖到家门口来了,再不用担心当天挑不完放在坡上受潮。去砍柴火也不再是一天一扛,而是用几天砍,几天捆,几天搬到公路边,然后三公的车子一车就把一年需要的柴火运回了家。搬运砖瓦、沙子、货物,到镇上赶集、上学,石三公的车都给予了极大的方便。
有一次,石三公去镇上拉货,半路刹车失灵,车子撞在坡榜上,有一片碎玻璃刺进了三公的脖子割破了颈动脉,据说血像喷管里的水一样往外射,村里人闻言一片愕然,无不为三公默默祈祷。三公人好,平日里给乡亲们拉货都是你愿意给多少是多少,从不计较路程远近,耗时长短,还帮你上货卸货,路上遇到挑重担的、晚归的不等招手就主动停在你身旁免费搭送。也许是好人有好报,石三公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被救活了。石三公遭此一劫,村里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动车了。然而三公病好之后,换了一辆小货车又重新当起了我们村的司机。他家里人都劝他说年纪大了,不要再开车了。三公说等有人顶替我的班了,我就休息。
八十年代末,开通了黎平至地理的班车。每天放学孩子们就会一排排的坐在街边的木楞子上守着班车经过,一听到喇叭鸣叫,所有目光就会齐刷刷地盯着村口,然后随着车子移动,一直移到望不见的远方,移到县城黎平。孩子们想,什么时候才能坐上这班车,去看看县城是什么样子。
1994年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黎平一中的民族班,终于从望着班车过往的孩子成为了班车内的一名乘客,第一次坐上了开往县城的中巴车。
班车从地里出来,经过好几个村寨才到我们村,车内拥挤不堪,充斥着各种气味,一上车,我的胃就翻腾起来,恶心想吐。父亲陪我去的,在车上,他的一个学生将坐位让给了他,父亲又将坐位让给了我。我坐下来,看着熟悉的村庄和山脉向后退去,紧闭口唇,将一切的情感都捂在了心里。
那天天气很好,可是头一天刚下过大雨,路面还很泥泞。班车开到需要上坡的地方就停了下来,车主叫女人小孩走到山顶上去等着,男人全部下车推车。巨大的中巴车,泥泞不堪的路面,长长的一段斜坡,男人们奋力地推着,没有一个人报怨,因为这是习以为常的事。看到这幅景象,我的眼睛潮湿了,我没有想到由乡间通往城市的路会这么艰难。
父亲送我到学校,将我安顿好就回去了。由于一路上车窗哐当哐当的响,我耳鸣了三天,休息了一个星期,鼻腔里的汽油味似乎仍没有散尽,生病一样晕晕呼呼。日后再看到那样又脏又破的中巴车,心里就不免升起一丝恐惧,可是,要在乡村与城市间往返,又不得不倚仗于它。
三
路是随着河流蜿蜒的。在挖机、炸药还没有普及到山村的年代,我们能够拥有一条凭借人力挖出的通车公路,主要是因为河流。
有山便有川,聪明的民族傍水而居,傍不到水,住在山腰上,那是出于生存的无奈。纵观南北,谁拥有的水域越宽,水质越好,谁就越容易走向文明和富有。然纵观古今,水质的好坏与物质的富有程度又似乎成不了正比。于城市而言,我们是山里人,于没有河流住在半山腰上的山民而言,小河又足以成为我们巨大的骄傲。
我们的小河,不过几十米宽的河床,随着山谷走势款款坎坎地流淌。平日里河水清澈明亮,可以于水中观蓝天白云,观两岸山石草木,观河底光洁的卵石,仿佛一位温婉娴静的姑娘,一路上走走停停,播撒勤劳与善良。山洪暴涨的时候,河水浑浊,湍流急下,又仿佛力大无比的粗莽汉子,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山中没有平庸的流水,水是山的眼睛与灵气。厚重的大山,因为有了小河的缠绕与掩映才显得既巍峨苍翠而又灵动含情。古朴的山村,因为有了小河的滋养而繁衍不息,于宁静中多了些喧闹,于平淡中多了些情趣。没有在山里生活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一条小河的美丽以及她的富饶。
我们的小河隶属长江水系,是长江水系一条支流的源头,一路上因不断有溪涧加盟而慢慢变大。小河在地里还是小溪,至梭等桥与后江(gāng)汇流才有了小河的模样,至孟彦两河交汇而始有名称孟彦河,成为黎平县六大河流之一。由地里流经我们村庄至孟彦的这一河段是没有名称的,当地人称之为江(gāng),比小溪大比河流小,能放排能畜水建小型电站的江(gāng)。
小河给村庄最先带来的实惠是灌溉与运输。干旱之年,河两岸的水车依呀呀转动起来,近些年抽水机轰隆隆响起来,干旱之年便依然是丰收之年。小河让山民摆脱了完全靠天吃饭的命运,给山民的生存提供了一道安全凭障。
小河随山势流淌,缓急不定、宽窄有变,撑不了船,但却可以放排。不通公路的时候,山里的木材都是以放排的方式运输出去的。河水如果太小,木材会一路被卡,如果涨水太大,又会被冲断损坏,或者跑得太快冲入大江里掌控不了造成损失。这就需要会观测天象,能够预测何时下雨,雨量有多大。据说我爷爷是这方面的行家,后来我三伯得了真传,给放排人预测了几次都恰到好处,以至于后来我三娘种什么何时种,村里的妇女都悄悄追随。但是山里的气候局部性强,太难把握,意外之事时有发生。听大人们说,有一年村里的年轻汉子们趁洪水逐渐退落的时候去放排,不曾想上游暴发了更凶猛的山洪,有两个躲避不及而被山洪永远吞噬了性命。后来,沿河的村寨都筑起了水坝,筑水坝主要用于发电,但开坝放排却降低了放排的风险。
小河给村庄带来的最大的实惠是夜里的光明。因为这条小河,我们比山上的村庄进入有电时代早三十年。我们村的电站坝于1972年建在村头的起凤山脚,距离村庄约有1公里。电站建起来后,不仅夜晚不用再点蜡烛与火把,还结束了村民舂米吃饭的历史。三伯是电站的守护人,每天早晨割完牛草就到电站去给村民打米,傍晚天快黑的时候开闸发电,深夜12点关电。三伯是胆大心细的人,至2002年并入南方电网,三十来风雨无阻,准时开电关电,总能在遭遇异常天气前及时断电,很少造成重大损失,使我们的电站成为了沿河所有电站中发电量最大最稳定的一个。三伯也因为他的能力与为人成为了村里威望最高最受好评的人,在村里担任了二十几年的村长支书,至今依然是我们村的老支书。
小河离村落很近,用水、洗涮、捕鱼、河滩上的晾晒,河流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办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更为山里孩子们的童年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孩子们在小河里追逐、嬉戏,站在小河边上望着潺潺远去的流水遐想,心里升起一些希望与梦想。诸如此类,有些影响是看不见的,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述的。山和水相依偎、相映衬、相点染的风景,早已成为山民祖祖辈辈最熟悉、最亲切、最美丽的背景与记忆。而当我们一步步走向城市,远离山村,这条清流也会永远荡漾在我们记忆的某个角落,距离越远越明澈,时间越久越清亮。
我为这条美丽的小河,滋养了我的村庄我的祖先的小河,装点了我的童年让我为之骄傲的小河没有名字而遗憾。我不甘心地访问了村里的许多老人,向他们打探这条小河最初的名字。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告诉我,说这条小河是有名字的,叫七子河。他说在祖辈的观念里,五男二女七子团圆,是人一生最圆满的幸福,是最兴旺而又和谐的繁衍,二是从地里到孟彦,河边上恰好坐落着七个村庄,因而祖先将这条小河叫做七子河。老师说还有一首古歌为证,遗憾的是,老师还没有为我找出古歌便仙逝了。我会继续查找古歌,不过不是为了证实小河的名字,有着如此美好寓意的名字,我在知道的那一刻已经欣然接受了。因为小河是村庄唯一的河流,只要说江(gāng)边,大家便知道所指,有没有名字无关紧要。但我想,当村里人走出去,要将这条小河与别的河流区分开时,七子河的名字一定会被大家欣然接受。
四
在与周边村落相比较而自许为“小北京”的我的家乡芒岭村,因为居住相对集中、有公路有河流,无疑比其他民族村寨更早地走向了文明。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与日常生活习惯上。
我们虽是侗族,但到我父母一辈就已经全部说客话(即汉话,我们侗族人管汉族人叫客家)了,而且是纯正的客话口音,不像八柳宰佃的还夹着侗话的腔调,更不像再远一点的地里,很多人根本就不会讲客话,甚至都听不懂。听不懂客话,说明没过见世面,说明原始落后!为体现我们的文明,我们不再说侗话,不再穿侗衣,不再梳侗家人的头式,不再过侗族人的节日,我们已完全像汉族人一样生活,并以此为骄傲,而看不起那些说着少数民族语言、穿少数民族服装、生活习惯依然不改的民族同胞。在那个原始落后的山区,我们一度感到优越,感到自豪。
但让我们想不到的是,进入21世纪后,有人提出了“原生态”的概念,倡导保护和宏扬生态文明。大量的优惠政策倾斜向了那些未开化或者发展落后的地区。国家免费接通了电网,免费修通了公路,扶持生态产业,开发旅游资源。那些原本越是落后的地区,越成了打造的重点,因为不开化,他们还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性。而我们的村民祖祖辈辈是侗族,但现在已经集体不会讲侗话,不会唱侗歌,不会蜡染刺绣,我们的村庄已经没有了一点侗民族的特性。当别的村庄因发展旅游业纷纷修了油路时,通往我们村庄的路却依然是上世纪七十代的那条土泥巴路。那条曾经让人骄傲的路,现在却仿佛一种耻辱刺痛着它过往的村庄。
时常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民族?侗族。会讲侗话吗?不会。侗歌呢?不会。蜡染,你们那有吗?没有。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一股深深的悲凉与疼痛。
但有一点让我依旧骄傲的是,发展公益事业,比如修路、修建自来水之类,我们那里的村民不会计较个人得失,主动投工投劳,积极争取,因为他们相信要建设好家园靠的是自己。如果你做过基层工作,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慨,那些得到帮扶越多的村寨,等要靠思想越严重。有一条几公里的通村公路,从启动到修通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宁愿大家没有路走,也不愿损失自己的一棵树。有帮扶单位送了一些水泥要帮某个自然寨修一条到码头的水泥路,但最后因为征收不到运费,也没有人愿意投工投劳而放弃了。我曾在一个民族乡镇工作过,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似乎任何公益事业,都是公家的事,不关乎个人。
我想,发展是需要引导的,又或者不能过度的引导。
黔东南莽莽苍苍的大山里,仿佛天母随意播撒的种子散落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村寨,它们以山为屏障,以森林为掩护,像一个个处子安详而恬静地躺在大山宽阔的怀抱里,因为大山的滋养与阻隔,她们美丽、穷困而又无知。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的角逐,她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自己的奋斗,也就有了自己的疼痛与骄傲。
四周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山里人根据田土的分布而居,大的村落几百户,小的十几户甚至独家村。我们的村庄有两百多户人家,而且居住非常集中,这对于几个邻近都只有几十户的村落来说,可谓是大地方了。记得小时候流行这样一句儿歌“八柳宰佃猪牛圈,芒岭大队小北京”。没错,我们的村庄就叫芒岭。这句不知何人何时创造,怎样流行起来的俗语是我们小时候的骄傲,每当跟八柳宰佃的孩子们发生矛盾时,我们就故意大声哼唱,甚至不惜时常为此分成两个帮派干上一场。
芒岭,谁也说不清这个名字的由来。我浪漫地猜想,或许是我们的祖先逆江而上,逃难于此时,这座山岭正漫山遍野的开满芒草花,我们的祖先一下子喜欢上了这块美丽而又肥沃的土地,于是安居下来,芒岭因此而得名。村里的老人不同意我的说法,他们说这芒,是芒粑的芒,好多饥荒的年代,到处饿殍遍野,可我们地方从来没有人被饿死,因为我们的山上到处都是蕨菜,而且又懂得将蕨根制作成芒粑,芒岭应是因为这芒粑而得名。
芒粑,就是用蕨根,也叫芒根制作的粑粑。母亲说她七岁的时候就跟外婆上山挖芒根了,而父亲说他们小时候因为吃了太多的芒粑总是全身浮肿。全家人喜欢调侃的一件事是关于五叔的。五叔那个时候还很小,大概四五岁吧,每次叫他吃饭,他就会问,吃什么饭?芒粑。揍你娘,又吃芒粑。嫩声嫩气的骂语让人听着又好笑又心疼。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似乎懂得提起一切植物淀粉的方法。小时候家里粮食不够吃,母亲就将红薯、洋芋、南瓜之类做成糕点,比米饭还好吃。没有油,那些难以下咽的菜,根类、茎类、叶子,她都能做成豆腐或者原子,拌上辣椒姜蒜,美味无比。印象最深的,是山上的一种树叶做成的绿色豆腐,味道微苦,还有点涩,但晶莹剔透,十分诱人,母亲说这道菜能够降火利尿,还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鼓励我们多吃。母亲唯独没再做过一次芒粑。虽然我们生长在这个因芒粑而得名的村庄,却没见过芒粑长什么样,出于好奇,我们多次央求妈妈做来偿一偿,可妈妈总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好东西,还做什么芒粑呀,只要想起那个气味我胃就痛。
后来在餐馆里吃到用油精心煎炸过的芋色的芒粑块,那份酥香软糯真是叫人难忘,想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吃到骂娘呢?母亲说,没有油没有盐没有肉掺着炒,你们吃一块试试?母亲不再做芒粑,也许是不愿揭开那痛苦的回忆。但现在时代不同了,那些以前觉得难以下咽的东西,现在摆到桌上却能成为一道独特的美味。而我们现在桌上的许多独特美味,又恰是人们在那些艰苦的年代为免除饥饿而提炼的智慧的结晶。
二
两三里路的距离在城市里比不上一个小区大,但在我们这却坐落着好几个独立的村寨。八柳离我们村大约有三里路程,而中间还隔着大宰佃与小宰佃。八柳座落在一个小山丘上,因而横穿我们寨子中心的马路只是路过他们的山脚,而宰佃距马路还要远一点,在一个山冲里。寨与寨之间,喊一嗓子都能听见,两山的住户,出了门就能相互望见,可是,要从一个寨子走到另一个寨子,要从你家来到我家,却不是那么方便的事,需要在迂回曲折的田埂地埂上绕来绕去才能到达。
在这里,更能让人体会到交通带给人类的骄傲。
我们村庄只因为有了那么一条窄窄的乡间马路,而使我们拥有着巨大的自豪。我们可以骄傲地对那些挑着担子,一摇一晃,艰难地从高山上下来的人大声说:这些山上佬!就好像城里人经过我们身边时,轻蔑地说:这些乡巴佬!山上的姑娘如果能够嫁到沿河一带的村庄,那是多么大的福气与荣耀。如果沿河村庄里的姑娘看上了山上的小伙子,哪怕小伙子人很优秀,也定会遭到家人甚至家族的反对。山里人谁不偿尽了没有路的艰难?谁不想走宽阔的路啊!哪个地方最先拥有宽阔的路,哪个地方的发展就会走在前面。
穿过我们村庄的公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凭人力一铲一锄挖出来的,全是义务工,一个村寨负责几公里,那些座落在山腰上的小村小寨自然没有能力将公路修到屋脚,只能继续过着凭脚力艰难生活的日子。其实我们的生活也依旧多是凭借脚力,虽然沿河有几片坝子田,但更多的田土在山上,山里人每天要烧的柴火、换油盐肥料的林木都在山上。不一样的是,有了公路,通往城市的距离就近了,换言之,通往发达与文明的距离就近了。
通公路后,我们村子里第一个买车的人是石三公,比八柳、宰佃、地里有第一辆车的时间都要早。学校里的孩子总是喜欢攀比,比奇事、比发展,七嘴八舌,一个声音比一个声音响亮。芒岭的孩子们说,我们村有车了,你们村有么?只此一句,别村的孩子就哑口了。
石三公将他的拖拉机开回村子的那天,许多人都来放炮祝贺,宴席从街头一直摆到街尾。从此,村里每天都会响起隆隆的机动车声,村里人的生活也随着这隆隆的声音悄悄地起了变化。秋收的时候,人们用麻袋装好稻谷背到公路旁,然后三公的车子隆隆隆就拖到家门口来了,再不用担心当天挑不完放在坡上受潮。去砍柴火也不再是一天一扛,而是用几天砍,几天捆,几天搬到公路边,然后三公的车子一车就把一年需要的柴火运回了家。搬运砖瓦、沙子、货物,到镇上赶集、上学,石三公的车都给予了极大的方便。
有一次,石三公去镇上拉货,半路刹车失灵,车子撞在坡榜上,有一片碎玻璃刺进了三公的脖子割破了颈动脉,据说血像喷管里的水一样往外射,村里人闻言一片愕然,无不为三公默默祈祷。三公人好,平日里给乡亲们拉货都是你愿意给多少是多少,从不计较路程远近,耗时长短,还帮你上货卸货,路上遇到挑重担的、晚归的不等招手就主动停在你身旁免费搭送。也许是好人有好报,石三公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被救活了。石三公遭此一劫,村里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动车了。然而三公病好之后,换了一辆小货车又重新当起了我们村的司机。他家里人都劝他说年纪大了,不要再开车了。三公说等有人顶替我的班了,我就休息。
八十年代末,开通了黎平至地理的班车。每天放学孩子们就会一排排的坐在街边的木楞子上守着班车经过,一听到喇叭鸣叫,所有目光就会齐刷刷地盯着村口,然后随着车子移动,一直移到望不见的远方,移到县城黎平。孩子们想,什么时候才能坐上这班车,去看看县城是什么样子。
1994年我以全镇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黎平一中的民族班,终于从望着班车过往的孩子成为了班车内的一名乘客,第一次坐上了开往县城的中巴车。
班车从地里出来,经过好几个村寨才到我们村,车内拥挤不堪,充斥着各种气味,一上车,我的胃就翻腾起来,恶心想吐。父亲陪我去的,在车上,他的一个学生将坐位让给了他,父亲又将坐位让给了我。我坐下来,看着熟悉的村庄和山脉向后退去,紧闭口唇,将一切的情感都捂在了心里。
那天天气很好,可是头一天刚下过大雨,路面还很泥泞。班车开到需要上坡的地方就停了下来,车主叫女人小孩走到山顶上去等着,男人全部下车推车。巨大的中巴车,泥泞不堪的路面,长长的一段斜坡,男人们奋力地推着,没有一个人报怨,因为这是习以为常的事。看到这幅景象,我的眼睛潮湿了,我没有想到由乡间通往城市的路会这么艰难。
父亲送我到学校,将我安顿好就回去了。由于一路上车窗哐当哐当的响,我耳鸣了三天,休息了一个星期,鼻腔里的汽油味似乎仍没有散尽,生病一样晕晕呼呼。日后再看到那样又脏又破的中巴车,心里就不免升起一丝恐惧,可是,要在乡村与城市间往返,又不得不倚仗于它。
三
路是随着河流蜿蜒的。在挖机、炸药还没有普及到山村的年代,我们能够拥有一条凭借人力挖出的通车公路,主要是因为河流。
有山便有川,聪明的民族傍水而居,傍不到水,住在山腰上,那是出于生存的无奈。纵观南北,谁拥有的水域越宽,水质越好,谁就越容易走向文明和富有。然纵观古今,水质的好坏与物质的富有程度又似乎成不了正比。于城市而言,我们是山里人,于没有河流住在半山腰上的山民而言,小河又足以成为我们巨大的骄傲。
我们的小河,不过几十米宽的河床,随着山谷走势款款坎坎地流淌。平日里河水清澈明亮,可以于水中观蓝天白云,观两岸山石草木,观河底光洁的卵石,仿佛一位温婉娴静的姑娘,一路上走走停停,播撒勤劳与善良。山洪暴涨的时候,河水浑浊,湍流急下,又仿佛力大无比的粗莽汉子,蕴藏着巨大的能量。
山中没有平庸的流水,水是山的眼睛与灵气。厚重的大山,因为有了小河的缠绕与掩映才显得既巍峨苍翠而又灵动含情。古朴的山村,因为有了小河的滋养而繁衍不息,于宁静中多了些喧闹,于平淡中多了些情趣。没有在山里生活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一条小河的美丽以及她的富饶。
我们的小河隶属长江水系,是长江水系一条支流的源头,一路上因不断有溪涧加盟而慢慢变大。小河在地里还是小溪,至梭等桥与后江(gāng)汇流才有了小河的模样,至孟彦两河交汇而始有名称孟彦河,成为黎平县六大河流之一。由地里流经我们村庄至孟彦的这一河段是没有名称的,当地人称之为江(gāng),比小溪大比河流小,能放排能畜水建小型电站的江(gāng)。
小河给村庄最先带来的实惠是灌溉与运输。干旱之年,河两岸的水车依呀呀转动起来,近些年抽水机轰隆隆响起来,干旱之年便依然是丰收之年。小河让山民摆脱了完全靠天吃饭的命运,给山民的生存提供了一道安全凭障。
小河随山势流淌,缓急不定、宽窄有变,撑不了船,但却可以放排。不通公路的时候,山里的木材都是以放排的方式运输出去的。河水如果太小,木材会一路被卡,如果涨水太大,又会被冲断损坏,或者跑得太快冲入大江里掌控不了造成损失。这就需要会观测天象,能够预测何时下雨,雨量有多大。据说我爷爷是这方面的行家,后来我三伯得了真传,给放排人预测了几次都恰到好处,以至于后来我三娘种什么何时种,村里的妇女都悄悄追随。但是山里的气候局部性强,太难把握,意外之事时有发生。听大人们说,有一年村里的年轻汉子们趁洪水逐渐退落的时候去放排,不曾想上游暴发了更凶猛的山洪,有两个躲避不及而被山洪永远吞噬了性命。后来,沿河的村寨都筑起了水坝,筑水坝主要用于发电,但开坝放排却降低了放排的风险。
小河给村庄带来的最大的实惠是夜里的光明。因为这条小河,我们比山上的村庄进入有电时代早三十年。我们村的电站坝于1972年建在村头的起凤山脚,距离村庄约有1公里。电站建起来后,不仅夜晚不用再点蜡烛与火把,还结束了村民舂米吃饭的历史。三伯是电站的守护人,每天早晨割完牛草就到电站去给村民打米,傍晚天快黑的时候开闸发电,深夜12点关电。三伯是胆大心细的人,至2002年并入南方电网,三十来风雨无阻,准时开电关电,总能在遭遇异常天气前及时断电,很少造成重大损失,使我们的电站成为了沿河所有电站中发电量最大最稳定的一个。三伯也因为他的能力与为人成为了村里威望最高最受好评的人,在村里担任了二十几年的村长支书,至今依然是我们村的老支书。
小河离村落很近,用水、洗涮、捕鱼、河滩上的晾晒,河流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办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更为山里孩子们的童年增添了无限的乐趣。孩子们在小河里追逐、嬉戏,站在小河边上望着潺潺远去的流水遐想,心里升起一些希望与梦想。诸如此类,有些影响是看不见的,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述的。山和水相依偎、相映衬、相点染的风景,早已成为山民祖祖辈辈最熟悉、最亲切、最美丽的背景与记忆。而当我们一步步走向城市,远离山村,这条清流也会永远荡漾在我们记忆的某个角落,距离越远越明澈,时间越久越清亮。
我为这条美丽的小河,滋养了我的村庄我的祖先的小河,装点了我的童年让我为之骄傲的小河没有名字而遗憾。我不甘心地访问了村里的许多老人,向他们打探这条小河最初的名字。我小学的启蒙老师告诉我,说这条小河是有名字的,叫七子河。他说在祖辈的观念里,五男二女七子团圆,是人一生最圆满的幸福,是最兴旺而又和谐的繁衍,二是从地里到孟彦,河边上恰好坐落着七个村庄,因而祖先将这条小河叫做七子河。老师说还有一首古歌为证,遗憾的是,老师还没有为我找出古歌便仙逝了。我会继续查找古歌,不过不是为了证实小河的名字,有着如此美好寓意的名字,我在知道的那一刻已经欣然接受了。因为小河是村庄唯一的河流,只要说江(gāng)边,大家便知道所指,有没有名字无关紧要。但我想,当村里人走出去,要将这条小河与别的河流区分开时,七子河的名字一定会被大家欣然接受。
四
在与周边村落相比较而自许为“小北京”的我的家乡芒岭村,因为居住相对集中、有公路有河流,无疑比其他民族村寨更早地走向了文明。这主要体现在我们的语言与日常生活习惯上。
我们虽是侗族,但到我父母一辈就已经全部说客话(即汉话,我们侗族人管汉族人叫客家)了,而且是纯正的客话口音,不像八柳宰佃的还夹着侗话的腔调,更不像再远一点的地里,很多人根本就不会讲客话,甚至都听不懂。听不懂客话,说明没过见世面,说明原始落后!为体现我们的文明,我们不再说侗话,不再穿侗衣,不再梳侗家人的头式,不再过侗族人的节日,我们已完全像汉族人一样生活,并以此为骄傲,而看不起那些说着少数民族语言、穿少数民族服装、生活习惯依然不改的民族同胞。在那个原始落后的山区,我们一度感到优越,感到自豪。
但让我们想不到的是,进入21世纪后,有人提出了“原生态”的概念,倡导保护和宏扬生态文明。大量的优惠政策倾斜向了那些未开化或者发展落后的地区。国家免费接通了电网,免费修通了公路,扶持生态产业,开发旅游资源。那些原本越是落后的地区,越成了打造的重点,因为不开化,他们还保持着本民族的特性。而我们的村民祖祖辈辈是侗族,但现在已经集体不会讲侗话,不会唱侗歌,不会蜡染刺绣,我们的村庄已经没有了一点侗民族的特性。当别的村庄因发展旅游业纷纷修了油路时,通往我们村庄的路却依然是上世纪七十代的那条土泥巴路。那条曾经让人骄傲的路,现在却仿佛一种耻辱刺痛着它过往的村庄。
时常有人问我,你是什么民族?侗族。会讲侗话吗?不会。侗歌呢?不会。蜡染,你们那有吗?没有。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到一股深深的悲凉与疼痛。
但有一点让我依旧骄傲的是,发展公益事业,比如修路、修建自来水之类,我们那里的村民不会计较个人得失,主动投工投劳,积极争取,因为他们相信要建设好家园靠的是自己。如果你做过基层工作,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慨,那些得到帮扶越多的村寨,等要靠思想越严重。有一条几公里的通村公路,从启动到修通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因为他们宁愿大家没有路走,也不愿损失自己的一棵树。有帮扶单位送了一些水泥要帮某个自然寨修一条到码头的水泥路,但最后因为征收不到运费,也没有人愿意投工投劳而放弃了。我曾在一个民族乡镇工作过,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似乎任何公益事业,都是公家的事,不关乎个人。
我想,发展是需要引导的,又或者不能过度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