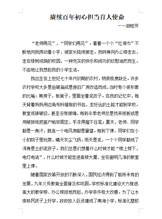生命中的河流
若水分享
1147
沂河
我对那些生活在不靠山不靠水的村庄里的孩子,总是禁不住心生怜悯。——没有水,看不见山,童心往哪里安放呢?
而我是幸运的。沂河从遥远的山中,从我人生的起点,流进我的生命里。她是我生命中的原血活水。
我的家其实就是河的一部分。涨水时节,水甚至会爬上河岸,冲刷墙基那红红的柳树根须。河水几乎常年都是恬静的,清澈的。到了夜里,沂河会将她特有的水音送至我的耳边。那种水音,在世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听到。条件太“苛刻”了——临河的土屋,粗糙的木格窗棂,泛着浓烈土腥味且多年未曾洗过的枕头,三四岁至十多岁的年龄,干瘦的小躯体躺在光光的苇席上,饿着肚子或胃袋里装着一些粗劣的食物,大脑里面则塞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口号,还有一位躺在另一张床上虽然年轻却整日气息奄奄的母亲。条件还有许多,只有那些条件都具备了,你才会听见那种声音。那种声音,你能听见吗?水在动,沙在动,河在动,天在动,地在动,我在呼吸,我活着。沂河知道我童心里的所有委屈和快乐。
沂河沙声地纯粹地歌唱着,奔流,奔流 。
那是沂河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有各种鱼,各种鸟,各种昆虫。河流的母性意义不言自明,故乡的河就更是如此了。不论从哪个方向接近沂河,感受都是一样的:土地越来越平坦,空气越来越柔和湿润,鸡鸣犬吠越来越密集,你听见了水声,看见了宽宽的河床,看见生灵们在河上的狂欢。它们全是沂河母亲抚育的孩子。
1997年春节刚过,我不得不把将要远赴新疆喀什支边的消息告诉我那顽强活下来的母亲。其时母亲正缠绵病榻,她不理解她的儿子何以要抛下她走那么远那么久。我抚着母亲的病躯,找不出话来安慰她。我走到沂河里,在那里默默地呆了很久,暮色降临时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说:“又去河里啦?除了脏水,什么也没有了。我有多少年不去河里了?糊涂了,不知道了。”在沂河边过了一生的母亲,竟有很多年不去抬步就到的沂河了。
母亲的衰病令我伤心,沂河面目全非同样令我伤心。清澈的水流没有了,鱼类几乎绝迹,鸟鸣声难觅,仅存的物种在量上也少多了。有许多曾与我的童年生活密切相关的美丽生命再也找不到了——它们可能已愤怒地绝迹了。这个世界已不配那么美好的生灵活着吗?河水仍在流,但流动声不一样了,不是纯净的声音了,不是愉快的声音了,是哭泣的声音,是呜咽。
水边仍有许多孩子——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许多孩子的。他们不下水,都穿着整洁,看上去比我的儿时幸福多了。可是,他们对沂河会产生我对沂河似的爱吗?面对清纯的对象人会产生清纯的爱,面对污浊的对象呢?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孩子们没有看见过异常美丽的沂河。孩子们啊,这如何是好?
这令我更加向往沂河的源头了。天下的河都有一个清澈的源头,正如人有一个清澈的童年,母亲有一个清澈的少女时代。我没见过任何一条河的源头,但我相信天下的河是同源的,都源自一个高远清洁的地方。可是,谁还能向我指出一条称得上清澈的河流呢?她们流着流着,流了千年万年,流到今天,全都变节了。不是变节了,是被人们羞辱了。
我没法对母亲说这样的话:去遥远的地方是为了寻找一条不变节的河流。
沭河
沭河是沂河的姊妹河。两河同源于沂蒙山,几乎是肩并肩走过沂蒙大地,走向山外的大海。她的形态与沂河也是相似的。
师专毕业那年,我不想回家乡去,天性中的漂泊愿望促使我想走得远一点。师专生的天空是狭窄的,想走远也走不远。我被分配到邻县的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就座落在沭河岸边。
我在她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她知道我青春的全部苦涩和欢乐。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许多细节和话语,全都随流而逝。妻却一直在我的身边。沭河给了我最低限度的尊严和最高的奖赏。
在水一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爱情是产生在水边的。《诗经》中的情诗常常与水有关。不过,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了。水边的爱情是越来越少了。
塔里木河
远离了沂河,远离了沭河,越过黄河,来到了塔里木河。
塔里木河是大地上最长的内陆河。她有庞大的水系。她接纳着来自昆仑山、天山、帕米尔高原的众多支流。我所在的喀什噶尔就是她是上游水系所孕育的一个着名绿洲。
我曾不避艰险奔波数千里,从她的上游出发,去探看她的中游下游。她的形态令人伤情。她不同于世上的任何一条河流。在从库尔勒至若羌的千里长途中,在胡杨、罗布麻、红柳、梭梭等沙漠植物的簇拥下,她时隐时现,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我来到了她的下游,她已疲惫到了极点。水流细弱滞钝,几乎看不出是在流动。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前,她还能流进浩瀚的罗布泊,后来她流进罗布荒漠,现在她连罗布荒漠也走不到了,在离昨日归宿很远的地方,她就脚步踉跄,力竭而死,如一声长长的叹息。
河流的样子表明河流都想走很远的路。世上河流的归宿总是一片大水——湖或者海,河流走到一片大水就没法再走了。我曾看见河流入湖入海的情景,那种开阔懒散的样子,仿佛表明那些河流的心情:不走了,这儿就很好。那些河流似乎寻找到了一个意义的汪洋。而塔里木河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她怀着强烈的想走下去的愿望却没法再走了。她生于雪域,死于荒漠。
塔里木河起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的高山雪域,然后沿北——东北——东——东南——南这一方向艰难推进,几乎把三分之二的大沙漠拥进了怀里。这是一位怀抱伟大妄想的温厚坚强的母亲。这大约是人世间一条最为负重累累的河。在世上最为寂寞的地方,她奋力挽起一条生命的长廊。莎车——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巴尔楚克——轮台——库尔勒——若羌等,这些珍珠般的绿洲都是塔里木河孕育的。楼兰、米兰等古代绿洲则是这位母亲不得不舍弃的孩子。
我在孤悬西陲的喀什噶尔绿洲度过了三年时光。从绿洲流过的塔里木河支流有三条:吐曼河、克孜勒河(古称赤水)、叶尔羌河。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傍城而过的吐曼河。我所供职的中学就在河的东岸,我每天要见她好多次。热爱河流的秉性促使我去探看她距城较远的河段。在我的维吾尔弟子阿布都的带领下,我们溯河而上,很快就看见了蜿蜒于大戈壁上的吐曼河。河两岸没有一棵树,也不能说有草,却有一群羊,放羊的是位喀丝巴郎(维语称姑娘)。羊群索索地前行,卷起漫天尘土,煞是壮观。羊吃什么呢?原来它们在寻觅从远处刮来的树叶,也小心地啮食骆驼刺较嫩些的尖部。羊也吃骆驼刺呀?我一直以为羊只吃草——我这样说道。骆驼刺也是草呀。——阿布都笑着纠正我。我恍然大悟——骆驼刺本来就是草呀。我早就发现,在南疆沙漠地带做头牲畜,也要比其他地方的牲畜更坚强一些才行。
传来了幽幽咽咽的歌声,是那位牧羊姑娘在唱。在喀什城乡,我每时每刻都能听见各种各样的维吾尔歌吹,对此差不多已经漠然,但这姑娘的歌声却特别,我想,这其中一定有深情的内容。我对弟子说:“你听,她唱的是什么意思?”阿布都凝神听了一会,说道:“这是木卡姆组曲中的一段,歌词大意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都是一个命吗?为了你的愿望,我愿为你去死亡。’”停了一下,阿布都将最后一句修正为“我愿为你去牺牲”。我知道木卡姆是维吾尔人有名的土风歌舞。几乎全是对爱情的向往与歌颂。这就是几句关于爱情的誓言。它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之后,我又走过一段很远的路,一直走到新疆最西南角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然后沿中巴公路走到了国境线,来到红其拉甫口岸。世上最为清澈的河流终于让我看见了——她就是塔什库尔干河。她源自雪域,由南而北,流入叶尔羌河,叶尔羌河又流入塔里木河。她流经的全程,海拔大都在4000米以上。我从喀什出发来到这里,每一公里海拔就上升7米多。这真可说是一片净土,高原,雪峰,激流,无不纯净。我终于摆脱了人类制造的所有垃圾。流在这样的地方,她的愉快心情一望而知:水量不大,冰凉彻骨,但激情奔放,婉转自如,她天真,她无畏,重要的是她清澈,彻底的清澈。从地图上判断,她可能就是塔里木河的正源。
这位雪域少女,后来成长为一位坚强的母亲 。
“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不都是一个命吗?为了你的愿望,我愿为你去牺牲。”
塔里木河,你教我追求清澈与坚强。
好好看一看那些河流吧。人们似乎忘了,人类就是在河流的教育下长大的。我爱这些河流,清澈的我爱,污秽的我也爱。污秽不是河的错,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们的错。那不是河的污秽,是你的污秽,是我的污秽,是大家的污秽。
我的河流,你的河流,大家的河流。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大家的。你不清澈,我不清澈,这世界如何才能清澈?
我对那些生活在不靠山不靠水的村庄里的孩子,总是禁不住心生怜悯。——没有水,看不见山,童心往哪里安放呢?
而我是幸运的。沂河从遥远的山中,从我人生的起点,流进我的生命里。她是我生命中的原血活水。
我的家其实就是河的一部分。涨水时节,水甚至会爬上河岸,冲刷墙基那红红的柳树根须。河水几乎常年都是恬静的,清澈的。到了夜里,沂河会将她特有的水音送至我的耳边。那种水音,在世上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听到。条件太“苛刻”了——临河的土屋,粗糙的木格窗棂,泛着浓烈土腥味且多年未曾洗过的枕头,三四岁至十多岁的年龄,干瘦的小躯体躺在光光的苇席上,饿着肚子或胃袋里装着一些粗劣的食物,大脑里面则塞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口号,还有一位躺在另一张床上虽然年轻却整日气息奄奄的母亲。条件还有许多,只有那些条件都具备了,你才会听见那种声音。那种声音,你能听见吗?水在动,沙在动,河在动,天在动,地在动,我在呼吸,我活着。沂河知道我童心里的所有委屈和快乐。
沂河沙声地纯粹地歌唱着,奔流,奔流 。
那是沂河的众声喧哗的时代,有各种鱼,各种鸟,各种昆虫。河流的母性意义不言自明,故乡的河就更是如此了。不论从哪个方向接近沂河,感受都是一样的:土地越来越平坦,空气越来越柔和湿润,鸡鸣犬吠越来越密集,你听见了水声,看见了宽宽的河床,看见生灵们在河上的狂欢。它们全是沂河母亲抚育的孩子。
1997年春节刚过,我不得不把将要远赴新疆喀什支边的消息告诉我那顽强活下来的母亲。其时母亲正缠绵病榻,她不理解她的儿子何以要抛下她走那么远那么久。我抚着母亲的病躯,找不出话来安慰她。我走到沂河里,在那里默默地呆了很久,暮色降临时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说:“又去河里啦?除了脏水,什么也没有了。我有多少年不去河里了?糊涂了,不知道了。”在沂河边过了一生的母亲,竟有很多年不去抬步就到的沂河了。
母亲的衰病令我伤心,沂河面目全非同样令我伤心。清澈的水流没有了,鱼类几乎绝迹,鸟鸣声难觅,仅存的物种在量上也少多了。有许多曾与我的童年生活密切相关的美丽生命再也找不到了——它们可能已愤怒地绝迹了。这个世界已不配那么美好的生灵活着吗?河水仍在流,但流动声不一样了,不是纯净的声音了,不是愉快的声音了,是哭泣的声音,是呜咽。
水边仍有许多孩子——这个世界上总会有许多孩子的。他们不下水,都穿着整洁,看上去比我的儿时幸福多了。可是,他们对沂河会产生我对沂河似的爱吗?面对清纯的对象人会产生清纯的爱,面对污浊的对象呢?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孩子们没有看见过异常美丽的沂河。孩子们啊,这如何是好?
这令我更加向往沂河的源头了。天下的河都有一个清澈的源头,正如人有一个清澈的童年,母亲有一个清澈的少女时代。我没见过任何一条河的源头,但我相信天下的河是同源的,都源自一个高远清洁的地方。可是,谁还能向我指出一条称得上清澈的河流呢?她们流着流着,流了千年万年,流到今天,全都变节了。不是变节了,是被人们羞辱了。
我没法对母亲说这样的话:去遥远的地方是为了寻找一条不变节的河流。
沭河
沭河是沂河的姊妹河。两河同源于沂蒙山,几乎是肩并肩走过沂蒙大地,走向山外的大海。她的形态与沂河也是相似的。
师专毕业那年,我不想回家乡去,天性中的漂泊愿望促使我想走得远一点。师专生的天空是狭窄的,想走远也走不远。我被分配到邻县的一所中学。这所中学就座落在沭河岸边。
我在她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她知道我青春的全部苦涩和欢乐。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许多细节和话语,全都随流而逝。妻却一直在我的身边。沭河给了我最低限度的尊严和最高的奖赏。
在水一方。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的爱情是产生在水边的。《诗经》中的情诗常常与水有关。不过,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了。水边的爱情是越来越少了。
塔里木河
远离了沂河,远离了沭河,越过黄河,来到了塔里木河。
塔里木河是大地上最长的内陆河。她有庞大的水系。她接纳着来自昆仑山、天山、帕米尔高原的众多支流。我所在的喀什噶尔就是她是上游水系所孕育的一个着名绿洲。
我曾不避艰险奔波数千里,从她的上游出发,去探看她的中游下游。她的形态令人伤情。她不同于世上的任何一条河流。在从库尔勒至若羌的千里长途中,在胡杨、罗布麻、红柳、梭梭等沙漠植物的簇拥下,她时隐时现,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我来到了她的下游,她已疲惫到了极点。水流细弱滞钝,几乎看不出是在流动。在短短的半个世纪前,她还能流进浩瀚的罗布泊,后来她流进罗布荒漠,现在她连罗布荒漠也走不到了,在离昨日归宿很远的地方,她就脚步踉跄,力竭而死,如一声长长的叹息。
河流的样子表明河流都想走很远的路。世上河流的归宿总是一片大水——湖或者海,河流走到一片大水就没法再走了。我曾看见河流入湖入海的情景,那种开阔懒散的样子,仿佛表明那些河流的心情:不走了,这儿就很好。那些河流似乎寻找到了一个意义的汪洋。而塔里木河的心情是怎样的呢?她怀着强烈的想走下去的愿望却没法再走了。她生于雪域,死于荒漠。
塔里木河起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南缘的高山雪域,然后沿北——东北——东——东南——南这一方向艰难推进,几乎把三分之二的大沙漠拥进了怀里。这是一位怀抱伟大妄想的温厚坚强的母亲。这大约是人世间一条最为负重累累的河。在世上最为寂寞的地方,她奋力挽起一条生命的长廊。莎车——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巴尔楚克——轮台——库尔勒——若羌等,这些珍珠般的绿洲都是塔里木河孕育的。楼兰、米兰等古代绿洲则是这位母亲不得不舍弃的孩子。
我在孤悬西陲的喀什噶尔绿洲度过了三年时光。从绿洲流过的塔里木河支流有三条:吐曼河、克孜勒河(古称赤水)、叶尔羌河。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是傍城而过的吐曼河。我所供职的中学就在河的东岸,我每天要见她好多次。热爱河流的秉性促使我去探看她距城较远的河段。在我的维吾尔弟子阿布都的带领下,我们溯河而上,很快就看见了蜿蜒于大戈壁上的吐曼河。河两岸没有一棵树,也不能说有草,却有一群羊,放羊的是位喀丝巴郎(维语称姑娘)。羊群索索地前行,卷起漫天尘土,煞是壮观。羊吃什么呢?原来它们在寻觅从远处刮来的树叶,也小心地啮食骆驼刺较嫩些的尖部。羊也吃骆驼刺呀?我一直以为羊只吃草——我这样说道。骆驼刺也是草呀。——阿布都笑着纠正我。我恍然大悟——骆驼刺本来就是草呀。我早就发现,在南疆沙漠地带做头牲畜,也要比其他地方的牲畜更坚强一些才行。
传来了幽幽咽咽的歌声,是那位牧羊姑娘在唱。在喀什城乡,我每时每刻都能听见各种各样的维吾尔歌吹,对此差不多已经漠然,但这姑娘的歌声却特别,我想,这其中一定有深情的内容。我对弟子说:“你听,她唱的是什么意思?”阿布都凝神听了一会,说道:“这是木卡姆组曲中的一段,歌词大意是‘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不都是一个命吗?为了你的愿望,我愿为你去死亡。’”停了一下,阿布都将最后一句修正为“我愿为你去牺牲”。我知道木卡姆是维吾尔人有名的土风歌舞。几乎全是对爱情的向往与歌颂。这就是几句关于爱情的誓言。它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之后,我又走过一段很远的路,一直走到新疆最西南角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然后沿中巴公路走到了国境线,来到红其拉甫口岸。世上最为清澈的河流终于让我看见了——她就是塔什库尔干河。她源自雪域,由南而北,流入叶尔羌河,叶尔羌河又流入塔里木河。她流经的全程,海拔大都在4000米以上。我从喀什出发来到这里,每一公里海拔就上升7米多。这真可说是一片净土,高原,雪峰,激流,无不纯净。我终于摆脱了人类制造的所有垃圾。流在这样的地方,她的愉快心情一望而知:水量不大,冰凉彻骨,但激情奔放,婉转自如,她天真,她无畏,重要的是她清澈,彻底的清澈。从地图上判断,她可能就是塔里木河的正源。
这位雪域少女,后来成长为一位坚强的母亲 。
“我的生命,你的生命,不都是一个命吗?为了你的愿望,我愿为你去牺牲。”
塔里木河,你教我追求清澈与坚强。
好好看一看那些河流吧。人们似乎忘了,人类就是在河流的教育下长大的。我爱这些河流,清澈的我爱,污秽的我也爱。污秽不是河的错,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们的错。那不是河的污秽,是你的污秽,是我的污秽,是大家的污秽。
我的河流,你的河流,大家的河流。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大家的。你不清澈,我不清澈,这世界如何才能清澈?